一封寫給俄羅斯的冬日長信











在畫廊里曾不止一次看到成群的小學生,由老師帶領著他們參觀,應該是政府鼓勵的一些教學活動,他們會在一些名畫前駐足,席地而坐,老師們則慢條斯理地傳授知識,與看著書本上的黑白圖片相比,哪一種教學方式更佳自有答案。或許是從小就侵染在藝術角落的緣故, 俄羅斯 人生性酷愛藝術,尤其是年輕姑娘,骨子裡似乎就散髮著藝術氣息,無論打扮還是談吐,也難怪在 俄羅斯 的總體感覺就是年輕姑娘的英語程度和綜合素質普遍高於男人,以及毛妹比警察靠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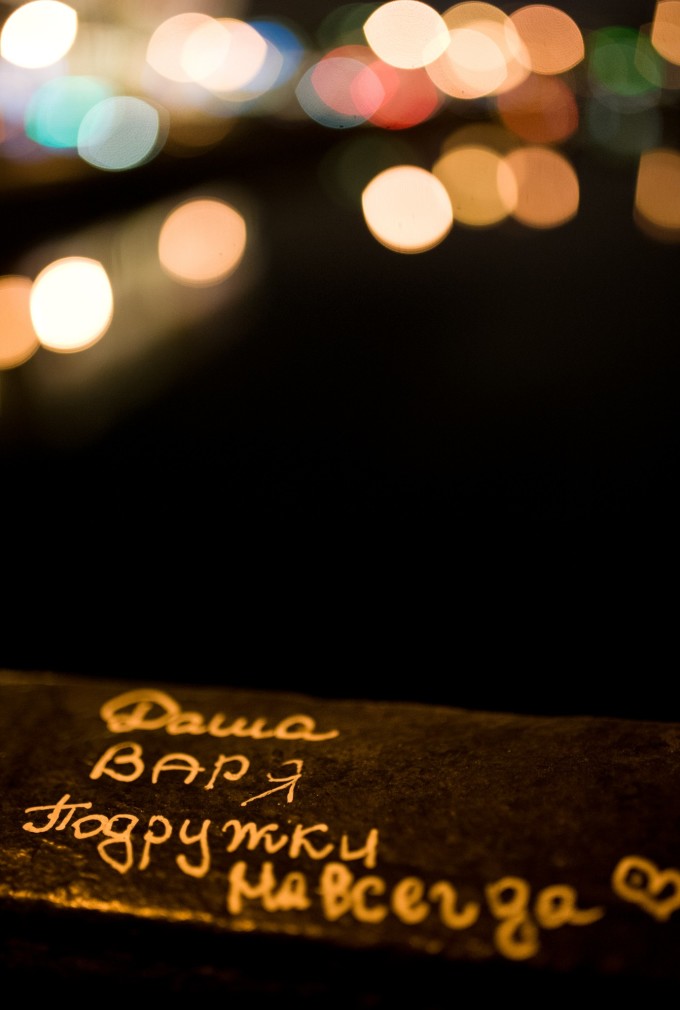



似乎所有初次來到 莫斯科 的游人都會選擇在阿爾巴特大街走上一遭,而阿爾巴特似乎又是許多文學家藝術家的靈感源泉,正如紅極一時的 莫斯科 游吟詩人布 拉特 •奧庫賈瓦所言:“阿爾巴特,我的阿爾巴特,你是我的事業,你是我的幸福與不幸”。果戈理、梅爾尼科夫和 普希金 也都在這條大街上打下過烙印,肖像畫家們聚集在街頭巷尾,身邊擺滿了自己的作品,另一端的吉他手和鼓手坐在路燈下為穿行而過的行人們賣力地表演著,這樣的景象使人們不得不將思緒又重新撥回到記憶里,不曾忘記那些老一輩的游吟詩人、街頭藝人、畫家和詩人在阿爾巴特留下的影子,就像不曾忘記曾經燒毀果戈理《死魂靈》手稿的那盞壁爐。
在我到達老阿爾巴特大街的時候天色已晚,肖像畫家們依然像白天一樣坐在自己的作品中央,偶爾起身活動,只是白天見證慘淡生意的手中報紙不見蹤影,有一家店面用中文寫著大字“保證天然 波羅的海 琥珀蜜蠟”,頓時失去進店逛逛的興趣; 非洲 雇佣者扮演玩偶在這冬夜裡辛苦地派發餐館傳單,口中操著和我俄語發音水平一樣的日語對我講著什麼;一位戴著墨鏡的彈唱者在這黑夜的路燈下賣力表演,所以我也分不清他到底是盲人還是裝酷,不過彈唱實力實在過硬,硬硬的俄語搖滾樂吸引了不少游客駐足,排成扇形,我在正當中,頗有一種彈弓將要發射的感覺,似乎和地理位置有關,在我淺薄的音樂知識里, 北歐 及 俄羅斯 這類寒冷地區更容易激發音樂者狂放的音樂細胞,需要用硬派表現力表達內心情感,淡淡的民謠吟唱聽不了一個開頭,轉眼就會變成狂嘶怒吼;一個哥們兒站在斜頂的房頂上,淡定地用鏟子清理積雪, 俄羅斯 人的戰鬥特性似乎體現在方方面面,手中的一切都是武器,配合嘴裡的念念叨叨,一板一眼地對付著面前的假想敵,哪怕只是屋頂的積雪;大街上不少禮品店都不可避免地出售著 俄羅斯 最有代表性的套娃,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這裡的套娃價格應該是整個 莫斯科 最貴的,有些套娃圖案粗糙地連我都可以畫得出來,卻也依然價格不菲;街中心有一座劇院,我路過的時候恰巧是進場之前,就像對 俄羅斯 中老年人以及名門望族的基本印象一樣,男人們穿著黑色板正西裝大衣,頭戴黑色帽子,手中拎著同樣黑色的皮質公文包,筆直站著抽煙捲,女人們則用貂皮大衣裹身,長靴及膝,手套過肘(我不知道這叫什麼),同樣筆直站著抽煙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