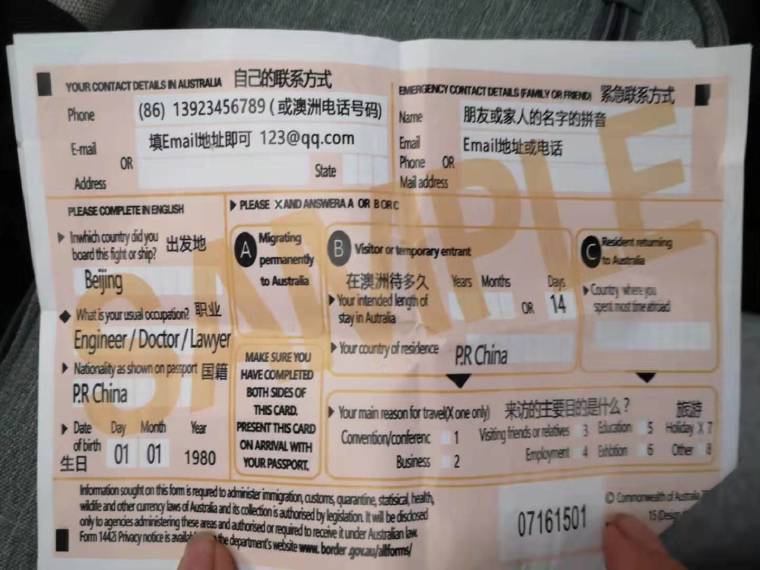多情的秘魯:21天大環線,4.5萬字花式游記,含馬丘比丘、亞馬遜雨林、的的喀喀湖




這是一片真正的,一望無際的沙漠,導游開始給車胎放氣,為接下來的沖沙活動做準備,我們車裡的幾個人也天南地北地聊起天來。
香港 姑娘今年大學畢業,獨自一人來到南美,原計劃兩個月走遍 秘魯 、 玻利維亞 、 智利 和 阿根廷 ,如今在 秘魯 一個國家就逗留了將近3個星期,而且沒有絲毫想離開的意思; 芬蘭 姑娘是一名公司職員,這次是利用年假出來旅行,在 秘魯 的行程和我們完全同步,連交通工具都是同一家公司的大巴,也是無巧不成書了。
我們也說起了自己的環球旅行,在 北京 的朋友圈裡每次說起這些大家都會嘖嘖稱奇,好像這是一件多麼困難、多麼不尋常、多麼了不起的事情,漸漸地我們也覺得自己是個另類的人;可是在旅途中遇到的朋友就不一樣了,大家的興趣和經歷都差不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是同類的人,我們的旅行在她們看來不過是件平常事,我們將來還會在某個地方相遇,也許是 秘魯 、也許是 阿根廷 、也許是南極或者外太空,我們的心不受束縛。
這件事兒說來也奇怪,這麼多同類的人,相見時相談甚歡,可即使互留了聯繫方式,還是相忘於江湖。
最終留在我們身邊的有技術宅,有循規蹈矩的上班族和家庭主婦,我們有著不同的生活軌跡,但我們卻是互補的。
有句話說:“相似的人適合一起歡鬧,互補的人適合一起變老。”
此刻想起來的確有幾分道理。







樂樂問我說:“什麼叫沖沙啊?”
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只聽“轟”的一聲,車子猛然提速沖向沙丘頂端,從立在地上的兩根竹竿之間穿行而過,等等!腳下不是懸崖嗎?我連忙抓著樂樂的手閉上了眼睛,只覺得一陣強烈的失重,我們從陡坡上“沖”了下來,緊接著“沖”上了另一個沙丘,再“沖”下來,我反問樂樂說:“這就是沖沙,好玩嗎?”
我第一次參加沖沙是在 埃及 的 撒哈拉沙漠 里,不過是比平時的車速快一些,顛簸一些,我怎麼也沒把這項活動和過山車聯想到一起,如今已經上了“賊車”,後悔也來不及了,團團和樂樂倒是玩得很開心,和大家一起尖聲大叫著,吃了滿嘴的沙子。
從車上下來的時候我的腿已經軟了,導游發給我們每人一個滑板,一個打磨滑板用的蠟塊,並簡單介紹了一下滑沙的姿勢:我們可以選擇坐著滑,或者趴著滑,小朋友如果害怕的話可以選擇和大人共乘同一個滑板。
樂樂考慮了很久,終於鼓足勇氣坐在了團團的滑板上,團團從身後抱著他,導游輕輕一推,兩個人飛快地滑了下去,我正在給他們錄視頻呢,只見滑板在接近沙丘底部的時候突然失去了平衡,樂樂從側面翻了出去,團團幾乎是越過樂樂的頭頂,翻到在了滑板的正前方,兩個人一臉迷茫地爬起來,對著我們揮了揮手。





樂樂再次展現了他好強的性格,輕描淡寫地回答說:“我摔了嗎?我就是故意在沙子里滾一滾,這沙子好暖和,好舒服啊。”
我用手摸了摸沙子,果然好暖和,好舒服。
我索性躺了下來,讓全身都緊貼在沙子上,心頭涌起一種莫名的幸福感,像一張緻密的蛛網,將我層層纏繞起來。
我想起了小時候和家人一起去內蒙的往事,想起了我和團團曾兩入 撒哈拉沙漠 ,在夕陽下騎馬,在星空下入睡。從愛上旅行的那一天起,我的行李越來越少,“家”這個概念也越來越淡泊。
我問樂樂說,你想家嗎?他毫不猶豫地說不想。
也許對他這個年紀的孩子來說父母就是家,那對我來說呢?
這是我有生以來離家最遠的一次,然而這裡的一切對我來說並不陌生,我看到了古代 秘魯 人建造的蓄水池和金字塔,他們為生存所做的努力和對信仰的虔誠,與我們的祖先又有什麼分別嗎?我們都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都曾面臨著自然條件的惡劣以及資源的匱乏,我們有很多東西都是互通的,不需要語言也能互相理解。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的祖先也是我們人類的祖先,“這裡”的風景也是我們地球上的風景,在浩瀚宇宙中我們都是同鄉。躺在這溫暖的沙丘上,我覺得親近而踏實。
如果有一天真的離開地球了,一切是否會不同?
現在的我,尚且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我想起了泰戈爾的一首詩:
“我旅行的時間很長,
旅途也是很長的。
天剛破曉,我就驅車起行,
穿遍廣漠的世界,
在許多星球之上,留下轍痕。
離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遠。
最簡單的音調,需要最艱苦的練習。
旅客在每一個生人門口敲叩,
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門;
人要在外面到處漂流,
最後才能走到最深的內殿。
我的眼睛向空闊處四望,
最後才合上眼說:“你原來在這裡!”
這句問話和呼喚“呵,在哪兒呢?”
融化在千股的淚泉里,
和你保證的回答“我在這裡!”的洪流,
一同泛濫了全世界。”
回程路上遇見了絢爛的晚霞,團團的頭髮被風吹得都立了起來,找家餐館吃頓像樣的大餐,等會兒還要趕夜間的大巴,前往下一座城市了。








1,如前文所說, 納斯卡 市郊沖沙、滑沙、金字塔、墓葬區等各個項目的旅行團到處都是,主街上走不了多久就能遇到一家旅行社,有半日游、1日游,也有多日游,價格都差不多,可收美金,語言不是問題。早點兒去可以報當天的團。我們報的團每人60索爾。
2,7月的天氣,白天有30多度,傍晚還是有點兒涼,尤其是坐在四面透風的車上,建議穿一件厚一點兒的外套。
3, 納斯卡 到下一站 阿雷基帕 的夜間大巴,依舊選擇Cruz del sur,晚上10點發車,實際上10點半才上車,11點才發車,目測是滿座,需要提前訂票。
阿雷基帕:雪山之巔的少女公元15世紀中葉,在印加帝國統治的區域里有一座海拔6310米的雪山Nevado Ampato,是當地的心目中的神靈所在。這是一個風雪交加的早上,貴族少女胡安妮塔在同行人的幫助下穿戴整齊,又開始了新一天的攀爬。
胡安妮塔今年12歲,是印加帝國里出名的美女,從小受到家人的精心呵護,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然而如今她不得不離開溫暖的家鄉,幾經輾轉來到這荒無人煙的雪山,同樣的攀爬已經持續了一周有餘,越接近山頂,天氣越寒冷,空氣也越稀薄,胡安妮塔的意識開始變得模糊起來。
從離家的那一天開始,無論是大大小小的祭祀活動還是這一場漫長的攀爬,胡安妮塔一直是眾人眼中的焦點,神聖而尊貴的“公主”。
然而她真的為此而感到驕傲嗎?
12歲的年紀或許還不足以讓她看透人生,卻足以讓她明白自己此刻的使命:她即將作為人間最珍貴的極品,被獻祭給雪山之神,希望能平息他的怒火,不再給這片大地帶來災難。
沒有人知道等待她的是什麼,她只有帶著對來世的憧憬,走完這最後一段旅途。
這一天終於還是來到了,在6000多米的雪山之巔,胡安妮塔穿上了印加帝國最精美的織錦華服,扣上了精緻的別針。同行的人為她梳理了每一根烏黑的長髮絲,編成辮子輕輕攏在背後,用黑色駝毛細線系在她的後腰帶上,紅白相間的羊駝毛披肩映襯她年輕的臉龐。她順從地接過一杯叫做奇卡(chicca)地玉米酒,一飲而下,隨即緊張地攥緊了衣角。
隨著右側眉骨上的一記重擊,她的生命定格在瞭如花似錦的12歲。
她從此安詳地長眠在山神的懷抱里,陪伴她的只有一些精緻小雕像,古柯葉和一些穀物。
直到500多年後的某一天,附近的另一座雪山Sabancaya大規模噴發,釋放出的熱量融化了Nevado Ampato山頂的部分積雪,使登頂再次變為可能。當地登山家Miguel Zarate在接近山頂的的地方發現了一些木質祭品的殘片,並 成功 說服了考古專家一同前往挖掘,終於讓胡安妮塔重新出現在了世人們的眼前。
她似嬰兒般捲縮著身體,由於始終處於冰凍的狀態,她的肌膚、身體組織和衣物幾乎完好無損,這對科學研究者們來說無疑是一個寶貴的資料庫。1995年,胡安妮塔被 美國 《時代雜誌》選為最重要的十大科學發現之一;1998年,在Nevado Ampato雪山附近的城市 阿雷基帕 建成了一座專題博物館,胡安妮塔的遺體從此被安放在這裡。
這個神秘而悲情的少女,正是我們來到這座城市的原因。
以下圖片來自網絡:

首先我們看了一部有關胡安妮塔和其他幾具木乃伊被髮現過程的紀錄片,隨後講解員帶我們進入了第一個展廳,這裡陳列著在Nevado Ampato以及附近雪山發現的祭祀用品,包括衣物、鞋子、腰帶、發飾、以及裝柯卡葉的小袋子等等,講解員心酸地介紹說,科學家們往往只能通過鞋子的尺寸來確定被獻祭給山神的兒童們的年齡,總共有幾十個之多,最小的只有四五歲。
接下來的展廳里主要陳列著屬於胡安妮塔的物品,最搶眼的是她紅白相間的披風, 美國 的紡織品專家威廉·康克林稱其為世界上最精美的印加織物,講解員說,在印加文化中紅色代表權力,白色代表純潔,紅白相間的衣物只有身份極其尊貴的人才有資格穿戴,所以專家們推測說,胡安妮塔的身份不止是貴族,她極有可能出身於王族。
在最裡面一間展廳的玻璃冰櫃里,我們看到了少女的真容,最讓人揪心的是她的右手,緊緊地攥著自己的衣角,這是緊張、痛苦還是決心呢?





醒來之後我第一件事就去找那個瓶子,可哪兒有什麼瓶子啊,一定是我對這少女心存同情,於是在夢裡給她安排了一個更好的結局。
然而相隔五百年,身處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中,我又如何能揣測,什麼才是對她最好的呢?
說來也邪門,在 秘魯 的這些天,不論我走到哪個城市,晚上總會做這個夢,離開了 秘魯 ,夢境也就隨之消失了。
實用信息:
1, 阿雷基帕 人口86萬,海拔2350米,走快了會有些累。
2,陳列冰凍少女的博物館:Meseo Santuarios Andinos,門票20索爾,周一到周六9am-6pm開門,周日9am-3pm,買票之後要等下一場參觀的時間,影片和展廳總共約1小時。 阿雷基帕:紅藍修道院到 阿雷基帕 的第一天主要是休整,只參觀了博物館和武器廣場,所有其他的景點都留給了第二天,所以特意起了個早。
我們的酒店在武器廣場旁邊,早飯後步行前往Santa Catalina修道院,之後簡稱紅藍修道院。這是今天的重頭戲,景點的面積之大,足以消耗2-3個小時的時間,與其說是修道院,倒不如說是個城中城。一路天氣很好,環城的3座雪山清晰可見,看到雪山便想到昨天的冰凍少女胡安妮塔,心中一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