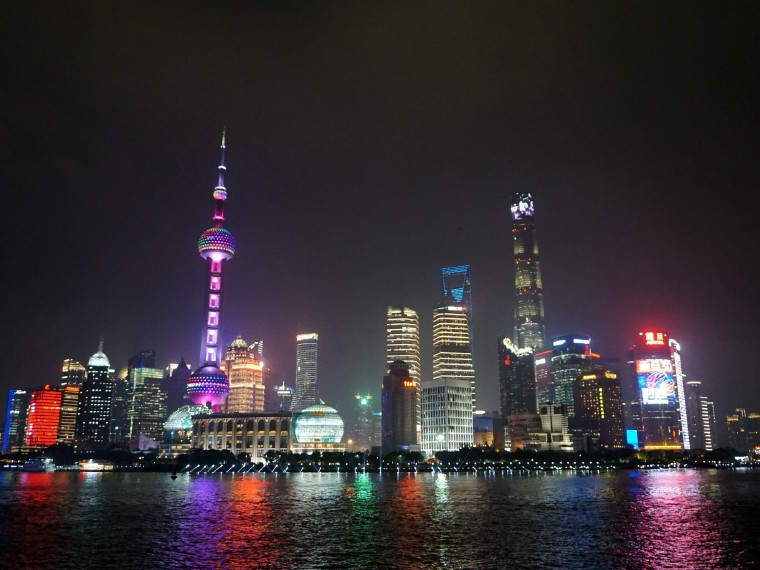上海丨赴一場十年之約







竈間之上,曬台之下,樓梯拐角間,有一個不起眼的小房間,稱為“亭子間”。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堆放雜物的雜物間。和通常認知的住房追求不同,這裡朝北,冬冷夏熱,面積狹小。不過精明的 上海 人怎麼會放過這個小房間呢,常常會出租增加收益。租住的人通常是剛到 上海 的人或者落魄的文藝界人士,魯迅、蔡元培、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這些知名人士都曾在亭子間里住過,併在這簡陋的環境里艱苦創作。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這是最好的座右銘吧。


果然對兒子是最好的。






二戰期間, 歐洲 的猶太人因《 紐倫堡 法案》的通過而被剝奪國籍使得他們淪為難民,更可悲的是幾乎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收留他們,只有 上海 ,無需簽證和任何官方文件許可就可以入境的口岸成為他們的依靠。據不完全統計,1933-1941年間,超過2.3萬猶太人難民以各種方式輾轉來到 上海 ,約1.4萬人居住在提籃橋一帶。1943年,日寇劃定了“無國籍南門限定居住區”,西起公平路、 東至 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隔離區里住著近10萬的從華北、蘇北逃難的人 民和 1937年後抵滬的猶太難民,水深火熱的時代中,逃難的 中國 人民毫無保留地接濟猶太難民,在他們在至暗時刻握住了一絲溫暖和堅毅,一起攜手 互助 共度時艱。
霍山路85號,由英商地產公司建於20世紀10-20年代之間,混磚假三層結構,毗連式建築,略具 英國 安妮女王時期建築風格特征。它的高光時刻莫過於遠東反戰大會在此召開過。1933年2月 中國 民權保障同盟籌備召 開遠 東大會,由宋慶齡擔任 上海 籌備委員會主席。9月底,遠東反戰大會在此秘密召開,正式成立了遠東反戰同盟 中國 分會,選舉宋慶齡為主席,促進了 中國 進步力量與世界發展力量的聯繫。

這幢極致對稱的古老房屋,即便多了些不太協調的空調外機、晾衣桿和雨棚,卻依然散髮著古典優雅的迷人氣息,令人流連忘返。

鮮有游人踏至,靜謐的街頭巷尾里洋溢著老 上海 的怡然自得。很慶幸霍山路與 舟山 路一帶維持著原有的風貌,保存著 上海 古老而鮮活的文化,靜靜地訴說著當年那段崢嶸歲月。









後來整理照片發現原來不經意間來過這片區域3次,只不過沒發覺罷了。


轉入 山西 北路,難得有大片的屋裡廂還沒被拆除。
富有歲月感的門匾上刻著的三個浮雕大字“ 康樂 里”。這片建於清末民初的石庫門裡弄,被列為了“不可移動文物”,免於被拆除的命運,並且可以到修繕與保護的寶貴機會。
康樂 里的主人是曾經擔任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處的“買辦”的潘氏家族。潘家與工部局可是有不解之緣,“買辦”身份沿襲了87年,傳承了5代。正因這個緣由,1908年前後工部局正積極開闢租界北區,潘氏家族順勢從工部局手中購得這片土地的所有權並籌建了 康樂 里。
列強對在 上海 的租界明裡暗裡進行了好幾次擴張,比較最大規模的一次是在1899年,當時公租界北區的西界從今 河南 北路沿線,擴展到 西藏 北路、 海寧 路、 浙江 北路沿線,北界則在“界路”(Boundary Road)今天目東路沿線。 康樂 里所在的 山西 北路(時稱北 山西 路)也划到了租界新界中。
說起天目東路,有個不得不提的重要地標 上海 火車站(後改稱為 上海 北站,今 上海 鐵路博物館,下一帕會提到)。5年之後的1904年“滬寧鐵路”全面動工建設,作為鐵路上重要交通樞紐 上海 站就建在天目東路與 寶山 路的交界處, 山西 北路的北端。當時租界在列強的開發下,經濟發展和市政建設較快,而且租界新界毗鄰繁忙的 上海 火車站,發展潛力巨大,用來發展房地產業前途無量。1914年 康樂 里建成,1916年,原滬寧鐵路和原滬杭鐵路並軌工程完工,滬寧鐵路 上海 站更名為 上海 北站,客貨運量驟增,成為 上海 名副其實的門戶, 康樂 里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所有者的特別身份,開啟了 康樂 里的高光時刻。
康樂 里作為買辦信用的產物,一來投資自住兩便;二來既方便家族間的聯絡,也減少了自己作為保人的風險。潘家的好幾房人層在此居住過,而後經過產權的更替,現在只剩下部分房產是貴潘家的四房、五房所有, 康樂 里的一代風華就此落下帷幕。

只可惜一道冰冷的鐵閘阻擋了探索的步伐,所以期待著某一天修繕結束後,能親身去體會其中的曼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