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鎖印尼ins深度玩法)那件瘋狂的小事叫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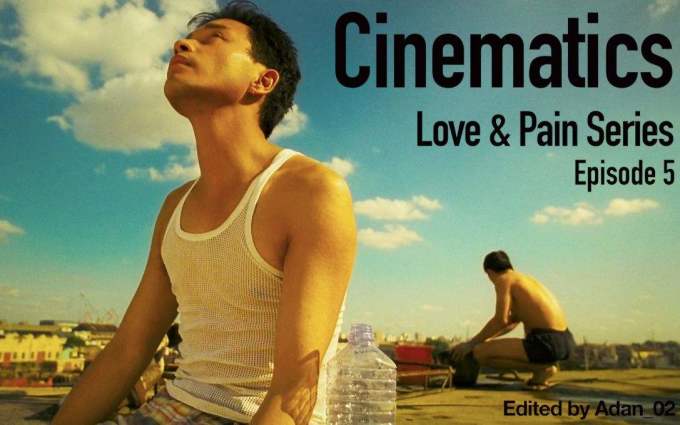

“在兩個人感情最好的時期,弗洛倫蒂諾• 阿裡 薩曾問自己,究竟哪一種狀態是愛情,是床上的顛鸞倒鳳,還是星期日下午的平靜。 薩拉 •諾列加用一個簡單的結論讓他平靜下來,那就是:凡赤身裸體乾的事都是愛。她說:"靈魂之愛在腰部以上,肉體之愛在腰部以下。" 薩拉 •諾列加覺得這個結論很好,可以用來寫一首關於貌合神離的愛情的詩。
——加西亞·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
“侯耀輝,不如我們從頭來過”。
《春光乍泄》在布利諾斯艾利斯的破爛旅館用了這樣一個激烈粗暴的同性之愛的場景開場,只是那時候侯耀輝處於主動的位置,而後,何寶榮躺在床上,悠悠地說:“侯耀輝,不如我們從頭來過”,侯耀輝就丟盔棄甲,盡釋前嫌了。
自此,何寶榮就像一個磨人的小妖精,倚仗著侯耀輝的愛,為所欲為,他“急切地盼望著可以經歷一場放縱的快樂,縱使巨大的悲哀將接踵而至,也在所不惜”。(太宰治《人間失格》)路上拋錨,侯耀輝下來推車,何寶榮頭也不回地發動汽車奔向遠方,然後點上一顆煙,停下來,像等一個偶遇的搭車人,那種眉眼裡的輕慢,張國榮演得不動聲色。他出入各種娛樂場所,和各色人等廝混,因為他篤定只要說出“不如我們從頭來過”這句話,侯耀輝就會站在原地毫無抵抗地原諒他,接納他。但他到底還是回了頭,在舞廳門口的時候,他眼見著侯耀輝做迎賓招待,他和他的新情人上了車,然後在汽車發動以後假裝漫不經心地回頭看了仍在門口徘徊的侯耀輝。
罪多者,其愛亦深。
面對侯耀輝的愛,他還是有愧疚的吧,所以偷了表來送侯耀輝,即使後來再要回去,也是被揍得鼻青臉腫的不得已。再後來,他一通電話將侯耀輝呼之即來,在醫院,他再次使出了殺手鐧“侯耀輝,不如我們從頭來過”。然後,二人重修舊好,他像一隻四處闖盪的小獸,在外受傷之後,回來蜷縮在侯耀輝的保護下,只管撒嬌說,抱抱我,我就是想你。
很多物件在劇中一再出現,很多場景在劇中一再渲染,而在王家衛鏡頭中 阿根廷 街頭的黑白、冷暖色彩的變化,都帶有莫名其妙的氛圍以及直指關鍵的隱喻含義。開場侯耀輝脖子上的一串鑰匙,他和何寶榮開開關關的寄居的小屋,以及後來侯耀輝給父親寄的問候卡片,電視里播報鄧小平離世,都在啟示一場疏離、漂泊、回歸的情路。
何寶榮受傷的那段日子,是侯耀輝最開心的時期。侯耀輝給他擦身,鋪床,噴除蟲劑,洗衣服,做飯,以及悄悄地藏起他的護照,害怕他不告而別,那些男女談戀愛時期喜歡做的事情,並沒有因為同性之愛有所區別。片頭橫亘在二人情愛之間涌動的 伊瓜蘇瀑布 的燈,侯耀輝一直帶在身邊,因為一次美麗的迷路,他們才又在 阿根廷 糾纏了許久。
天寒地凍的早晨,侯耀輝陪著何寶榮心血來潮去路邊搭車,想再次探訪 伊瓜蘇瀑布 ,仍是何寶榮在前,意氣風發的樣子,侯耀輝裹著衣服凍得縮手縮腳,但緊跟不棄。回到家裡發了高燒,還掙扎著起來給何寶榮煮飯。
輕風沉醉的夜晚,濃情纏綿的探戈。
有兩次侯耀輝在他工作的舞廳門口幫游客拍照的情景,一次,偶遇何榮華和情人出現在舞廳,侯耀輝氣急敗壞,摔手而去,另一次,何榮華躺在他的小屋裡,侯耀輝出門工作前撫摸他溫暖晨光中沉睡的眉,夜晚對著眼前擺pose的游客,按下手中的快門,說“笑一笑”。
沒有你,良辰美景可與何人說 。
可惜這樣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伴隨著何寶榮身體的複原,他又舊態復萌,夜晚著漂亮的衫遊蕩在街頭尋情艷遇,用受傷的手翻遍屋子尋找護照,他是那樣不甘寂寞,那樣急不可耐的想要離開,投身到活色生香的情欲世界里。
另一個同性戀傾向的暖男小張出現,不帶侵略性地介入他們的生活,他們像所有遭遇背叛危機的戀人一樣猜忌、質問、爭吵。侯耀輝買很多的煙,心照不宣地想要阻止何寶榮夜晚出街,而被何寶榮惱怒地橫掃在地,侯耀輝默默地撿拾起來煙盒,以一種固執的姿態輓留。
他們的交集大概於此。
艷陽下,侯耀輝在屋頂抹水泥,何寶榮用冰涼的水澆他的後背,依偎在他的頸背間親昵,侯耀輝怔怔地並無回應。樓下, 阿根廷 街頭人群各自歡娛,那是來自塵世的平凡瑣事與溫暖歡好。空中飛機轟鳴飛行,那是短暫地停留,又始終要離開的過程。一個想要停下來,一個想要繼續飛,結局,不言自明。
很愛王家衛對色彩、角度和景別的處理,一段侯耀輝在舞廳用玻璃瓶砸向何寶榮情人辭工回家路上紀錄片式的手持跟拍,緊張、不安、矛盾;另幾段,是侯耀輝和小張以及工友在午後烈日下踢球的手持跟拍,暖色光線,跳躍的人影,與小張之間,從搶球對罵到抱球傳遞到並肩作戰,推進著情緒的抒發宣泄和情感的悄然轉變。


他們終於在分開的路上越走越遠了。
何寶榮繼續流連情場。
侯耀輝換了一份工作,面對屠宰場被解剖的冰冷屍體,亦像是他自己支離破碎的身心,沖洗屠宰場,涌動的鮮血,也是愛痴情怨里自己受的傷,流的血。他也可以放浪形骸,以前他以為自己和何寶榮是不同的,後來才發現,原來人寂寞起來,也可以街頭求歡。誰和誰又有什麼不同呢。在骯髒的公共廁所,在各自的紛紛情欲里,擦肩而過,你我終成陌生人。
總要與過去有一個告別的吧。只是一個已決定結束,一個才想要從頭開始。
平行的蒙太奇手法,交待了各自在愛情里的抉擇。

侯耀輝去了二人那個美麗錯誤開始的地方,站在 伊瓜蘇瀑布 下,雨水混合著淚水,他很難過,他始終以為,站在著瀑佈下面的會是兩個人。
而這時,何寶榮搬回侯耀輝曾寄居的小屋,做當初侯耀輝為他做過的事情,買很多煙碼放得整整齊齊,整理房間,擦洗地板,修好了那盞 伊瓜蘇瀑布 的臺燈,才註意到燈罩里瀑佈下原是並肩站著兩個人的,痛哭流涕。


這一回,換何寶榮坐在門口守望掠過走廊的風,只是他的愛人,再也不會回來了。
“侯耀輝,不如我們從頭來過。”
侯耀輝終於沒有再給何寶榮說出這句話的機會。
和所有被消耗的愛一樣,隱忍的那個人終至決絕,這一次,換我先離開。
——————————————
看過《春光乍泄》以後,瀑布也不再是單純的風景,劇里是同性糾纏無望的愛,滾滾紅塵里歡好怨離輾轉徘徊,始終只有一個人站在瀑佈下。劇外,我和lee,一起走過荒漠無人的曠野,穿越山谷冷冽沉醉的風,並肩站在轟鳴的雨瀑下,這一生,兜兜轉轉,相愛的人總算沒有辜負。
Air terjun tumpan sewu lumajang環形瀑布,天氣好的時候可以拍到瀑布之後聳立的火山,它並不在瑪朗前往布羅莫的路上,也不妨礙我們特意包車繞道一去。


這裡不是成熟的觀景點,只有當地村民圈起來做了一些簡易的路引,正午到達,正是一天中較好的游完時間,也難遇到幾位游客。
去往大瀑布的路濕滑難走,先要下一段陡峭的樹樁和枯竹搭成的簡易臺階,再要淌一段流瀑,穿過亂石泥坡,才能看到轟鳴的瀑布裹挾著黃泥自環形的坑洞口湍流而下,六月並非雨季,還能有如此的水量,可以想象雨季到來之時,一定蔚為壯觀。


但這裡不只有這一個大瀑布,而是分佈著大大小小六七個瀑布,若非有嚮導帶領,常人並不容易找到。雖然主瀑布已足夠驚艷,其他小瀑布也各有特色,或清幽,或秀麗,或隱深,一路游玩驚喜不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