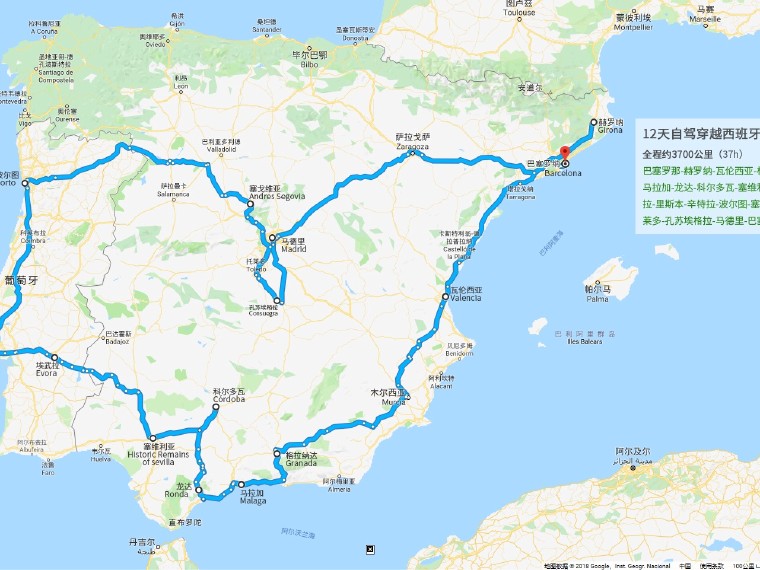阿爾漢布拉與腳下的 阿爾拜 辛一起伴隨著歷史走過了千年,遠方巍峨的內華達雪山在霧靄的籠罩下依舊若隱若現地挺立著。
天氣並不如意——天氣預報顯示今天有雨,更惱人的是,雨天將會持續到我離開 格拉納達 時。趁著天色還算敞亮,我匆匆趕往 聖尼古拉 斯眺望台,這是傳說中在 阿爾拜 辛遠望阿爾漢布拉的最佳視角。
還好,眼前雖有隨時變天的趨勢,但至少還算明朗。由於天氣的緣故,內達華雪山的身影並不分明。並不通透的光線中,阿爾漢布拉的陰影將歷史的沉重化作這座城市身後的迷霧向世人訴說著摩爾人時代的興衰榮辱。
聖尼古拉 丁更像是一處男女老少匯聚的大廣場,眼前是 西班牙 最輝煌、奢華的歷史見證,人們在休憩叫賣、肆意歌唱。這裡是 安達盧西亞 最驕傲的日落。每當日暮之時, 聖尼古拉 丁必定是整個 格拉納達 最具江湖氣的場所,各色人等都樂於在這裡享受光明消失前的熱烈與火艷。這種激情燃燒的熱情,正是 安達盧西亞 西班牙 最真實最動人最個性的一面不是麽。
阿爾拜 辛以北的Sacromonte,一度成為了吉普賽人的家園,即使時光的針腳走到如今,亦是如此。在穆斯林時代的最終, 格拉納達 完成了最終的謝幕,即使這尾聲總是帶著些許蒼涼、冷漠、羞恥。我想,正是由摩爾人在 格拉納達 休養生息的時間最長,潛移默化中也許 格拉納達 總是會帶著來自沙漠與烈火的狂野與不羈。
你要是問我,那現在呢?我大概還是會回答,是的。但正是由於這種不羈,使得 安達盧西亞 的奔放與野性在 格拉納達 詮釋地更加徹底與深刻。
弗拉明戈在 格拉納達 總是會與 西班牙 其他地區來得更加“狂野”,聚居在 聖山 的吉普賽人生根於 格拉納達 後把家安在了山坡上開鑿出的窯洞里,而生而自由奔放的吉普賽人與同樣不羈的 格拉納達 正好如烈火與浴血鳳凰那般產生了神奇的碰撞,窯洞中舞動的“Zambras”應運而生。
與 塞維利亞 的弗拉門戈相比, 格拉納達 的舞步來得更加奔放與熱烈。他們沒有華麗的彩服,也沒有精美的舞臺,就連舞者也比 塞維利亞 少一位。但是 格拉納達 的吉他更加憂郁,女人的聲線更加嘶啞,舞者腳下的舞步如 格拉納達 的石榴花一樣熱情四射,純正的吉普賽血統也許更能理解這個悲愴的民族的一路高歌后內心的苦楚,明白所謂生活就是在流離失所中為生存奔波。
雨中 聖山 ,透著清澈的涼意,行走在 聖山 頂點的教堂, 格拉納達 依舊是歷史叢林中從未失色的一枚綠松石。仙人掌肆意生長,就在向陽的一面,阿爾漢布拉冷靜守護著 格拉納達 。征服與被征服,榮耀與恥辱,歷史的循環樂此不疲,無論人類發展到了什麼樣的進程,曾經原始的欲望仍然如基因般世代留存。
這片空曠, 阿爾拜 辛、 聖山 、阿爾漢布拉,堅守與永恆,一步步從歷史走來。世界日新月異,但在 格拉納達 似乎時間放慢了老去的腳步,一切都停歇下來了。
聖山 的洞穴成為了流浪的吉普賽人的家園,即使現在,當你行走在濕潤的泥土山路上時,衣著襤褸卻鮮艷的吉普賽還是會嘴角上揚,對你送上一句“Buenos dias ”。
走在 格拉納達 的大街上,不難發現一座類似 塞維利亞 大教堂的建築,但你真的很難看清這座龐大建築的樣子——因為,這座建築物實在是太大了,更重要的是,周圍建築的局促性讓你更加難以平視這周遭的境地。
17世紀,由畫家成為雕塑家繼而成為建築師的阿隆索・卡諾建造,早在16世紀初 伊莎貝拉 與費爾南多就已經開始委托修建,但直到1704年才修建完工。
最終的建築呈現出的是一種混合風格:外部的巴 洛克 式,內部的文藝復興式,拱頂的純哥特式。
這座教堂宏偉巨大,滄桑中透著歷史的重量。在原有的清真寺地基上拔地而起的這座龐大建築物也算是見證了天主教接手這座城市之後的風風雨雨。宗教對於一個民族的影響,並不僅僅是一種。
與 格拉納達 教堂幾乎連為一體的另一座建築看似默默無聞的禮拜堂,可能是 格拉納達 最傑出的基督教建築了。然而,這看似平常的建築內,卻是 西班牙 歷史上最為傑出的雙王伊莎貝爾和費爾南多的陵寢,相比他們喧囂的一生,這裡要寧靜太多。
伊莎貝爾和費爾南多的遺體被安放在聖壇的 大理 石墓碑下,位於地下室內一個朴素的鉛棺內,雙王的鉛棺旁是他們的女兒瘋女胡安娜和她的丈夫菲利普的棺材。
陽光燦爛, 格拉納達 的大氣與野性構築的獨特氣質正是歷史所賦予的。
一座城市與一個人飛機降落在 巴塞羅那 機場時,窗外飄著密集雨點。我奮力將24寸的行李箱拖在拉巴爾區的窄巷中,我居然產生一種置身於某 南亞 國度的錯覺。是的,四周是 南亞 印巴面孔占領的各式小店,行走在 西班牙 語與印巴文字的大字招牌下,的確有一些心有餘悸。陌生的城市的夜晚,水汽蒸騰的霧氣蒙上了一層未知。
巴塞羅那 是恢弘大氣的,一路總能見到說不出名卻精緻的建築。
陰冷的哥特區,偶爾鴿子飛過。 羅馬 時代留下的刀光劍影留在冰冷牆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