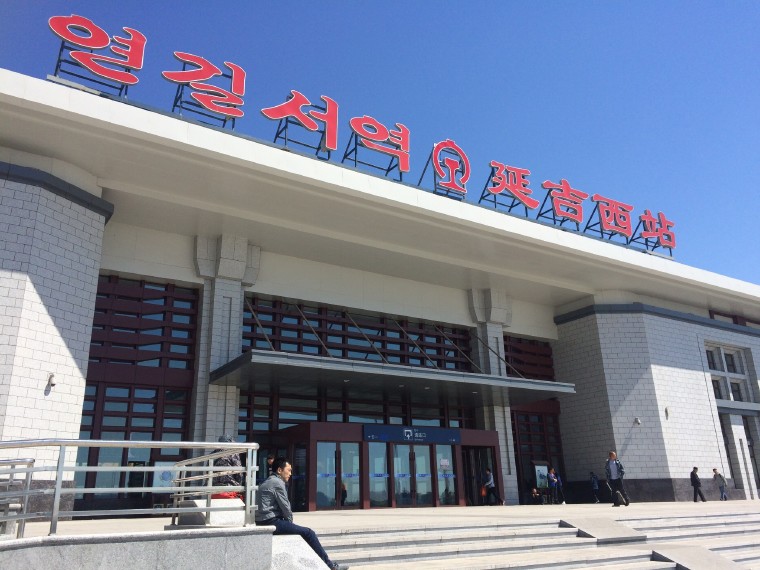西岸的亡靈河東岸的你·埃及

公元前30年,屋大維帶領 羅馬 軍隊入侵 埃及 ,克利奧帕 特拉 七世自殺,托勒密王朝覆滅, 埃及 進入 羅馬 人統治時期。
在島東部離神廟不遠處坐落著極具 羅馬 風格的建築—— 圖拉 真涼亭,又被稱為“法老王之床”,由 羅馬 皇帝 圖拉 真來此祭祀後修建。

然而不同宗教的融合和碰撞,同樣可能經歷溫和或者激進的多種可能,在 埃及 的神廟,經常可以看見基督教徒破壞的痕跡。他們鑿去原來的壁畫,又雕刻出基督教的符號。 東·開羅公元640年,阿拉伯人攻占 埃及 ,並於阿拉伯帝國後期先後出現法蒂瑪王朝和阿尤布王朝。法蒂瑪王朝統治期間,將首都定位 開羅 ,後因 薩拉 丁帶兵在擊退占領 埃及 的十字軍,法蒂瑪王朝哈里發被廢黜,公元1174年, 薩拉 丁建立阿尤布王朝並宣佈自己成為阿尤布王朝的第一位 蘇丹 ,在現今 開羅 舊城中心建造 薩拉 丁城堡。

清真寺外觀與 伊斯坦布爾 的藍色清真寺非常相像,只不過走近才能發覺這座清真寺真可謂“風塵僕僕”,外牆體皆是濃重的土黃色,頂部已分辨不出原色。

在這裡,古 埃及 五千年的文明已全然泯滅,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或許他們自己都說不清自己身體中流淌的到底是哪種血液,我無法評價這斷絕源頭的變遷究竟是好是壞,或許它只是歷史長河中一次偷了點小差卻又無二的抉擇,就好像基督教無法征服這片土地上的人卻面對五百年後才進入的伊斯蘭教俯首稱臣。
這是必然的進程,無關對錯。 結·沙漠·銀河過去的四年裡,每一年的四月我都會去一次沙漠,然後“歷經磨難”背回不同的沙子收集起來。倒並非刻意,更多的還是種巧合,只不過也許巧合多了也會成為必然。而對於現在的我來說,所謂必然就是這四年的每個四月,我都 會曬 成 非洲 黑人回來,然後面對衣櫃里色彩鮮艷花里胡哨的衣服陷入想穿而不敢穿捶胸頓足般的惱恨之中。

因為我們吃完午飯已經過四點,於是司機(其實是個車隊)決定直奔 白沙 漠,第二天上午返迴路上再去黑沙漠。從 巴哈利亞綠洲 去往 白沙 漠的路上就可以經過黑沙漠。

和大部分沙漠一樣,這裡在百萬年前也曾經是一片汪洋大海,氣候驟變海水退去,曾經的海底浮現出來。白色的石灰石在經年的風不停歇的打磨風化之下,一些裸露出地表,另一些早已碎成粉末,像雪片般灑落在黃沙之上,用手指不需多用力就能捏碎。

為了聽見風吹進心髒的聲音,為了一年一度最為嚮往的“奢侈”,為了能再一次全無障礙地仰望星辰,等待銀河融化在雙目之中就此消散,這裡便成為我選擇來 埃及 的唯一理由。

我們的司機——Hany車隊中大概年紀最大的、告訴了我他的名字卻被我忘記的大叔,自稱沙漠中的舒馬赫,或許可以稱為司機中最好的廚子、廚子里最好的司機——在路上和我們聊起了他的家庭,我們進沙漠的那天剛好是他6歲兒子的生日,他說他會在我們返回沙漠的那天去給他買一份禮物給他補過生日;在進入露營範圍時他讓我們閉上眼睛,然後睜開之時看到了夜色籠罩下一片滲透著冷光的白茫茫的“雪原”。
而當第二天到來,在我們這些游客於日出之後興奮地四處拍照的時候,他們要在尚有涼意的清晨做早飯。這是他們的人生。

“暴曬8日的 非洲 原住民”——留念。

黑沙漠是個非常容易帶給人錯覺的名字,真實的黑沙漠並非 冰島 的黑沙灘全是玄武岩碎片,而是像煤堆一樣僅在黃沙表層鋪陳著黑色砂礫,一座座山頭從地面升起。
其實它和 白沙 漠一樣,都是被黃沙覆蓋,只有高處才能顯露出本來面貌。

在這裡,能真切體會到何謂天堂與地獄,面前的黑沙漠像是座座火山口,在烈日之下,每一道黃沙堆砌出的紋理都像引導人邁向地獄入口的 通道 。
然而在千萬年前,在海水退去後而沙漠形成前的時代,這裡亦或許曾是一片沃土孕育著人類的生命。這也是為什麼左塞爾——第一座金字塔建於沙漠之中。

我們圍觀廚子司機大叔做飯時和他閑聊,他說自己做這行有十年了,前幾年來沙漠的游客並不多,近四五年才多了起來。然後他抬頭讓我們看月亮,他說他喜歡這月亮。
那天是初八的月,下午時分就早早懸在天上,我沒有告訴他我是來看銀河的,這樣的月光足夠讓我無功而返。

三點十分的鬧鐘響起時,我拎著三腳架和相機鑽出帳篷,直起身就看到月亮已垂至地平線不遠處,和午夜皎白的月色不同,即將落下的月光變得昏黃黯淡。
而轉過身,春季銀河就懸在當空,那般熠熠生輝。有那麼一刻,真的很想對它們說一聲“嘿,好久不見……”
然後或許它們也會眨眨眼對我答上一句,“嘿,如果真的是你請打招呼……”
……

春季的北半球並不是觀察銀河的最佳時間,接觸得越多,越感覺到第一次就能 成功 拍到銀河是多麼幸運的一件事。來之前的惴惴不安,聯繫不上Hany的心急火燎,鑽進睡袋後興奮的一時無眠,所有的一切情緒,在再度看到銀河的瞬間全部灰飛煙滅,剩下的只有滿足,和無法言說的震撼。
一年前的4月7日,我在納米布沙漠看到南半球的天,一年後的4月7日,我在這裡,在別人枕星而眠時,在這片天空之下,獨自一人與它們作伴。

寧可拖著快凍僵的身體一點點等待星塵的轉動,讓呼出的氣凝結成露留在這裡與此刻的星辰共存。本來我們的生命就來自星塵,最後也將歸於星塵。

也曾經在哪裡看過,若以尼羅河為銀河, 吉薩 的胡夫、哈拉夫和曼 卡拉 三座金字塔在地面的排列方位和天空中獵戶座三顆腰帶星的排列是完全一致的,但因為地球歲差的原因,它們所指向的並非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第四王朝,而是依據公元前1050年的天象而建。
彼時,當古老的 埃及 人生活在尼羅河東岸等待西岸逝去亡靈的歸來之時,他們同樣跨越了懸在夜空中的長河。而此刻,當我閉上眼睛感受4500年後的曙光,仿佛讀到了一種特別的東西
——一種人類情感在洪荒宇宙的見證之下所能展現出的最為極致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