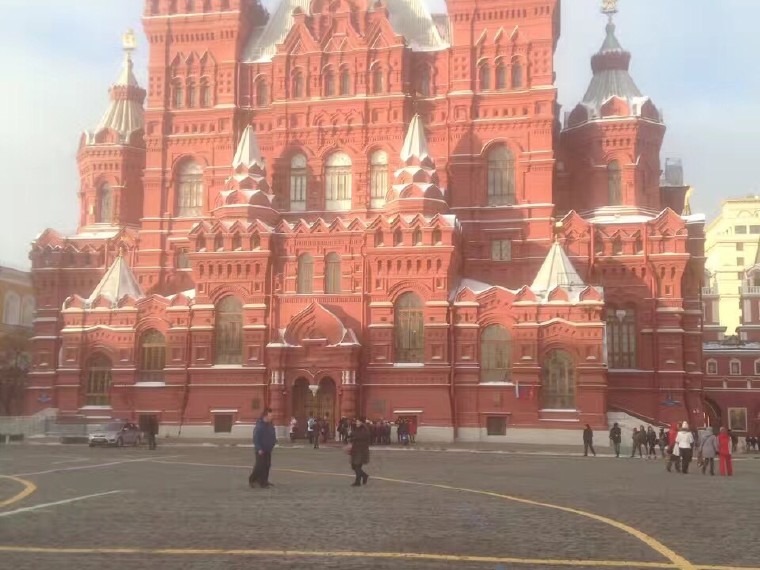我甚至覺得這不是埡口,更像是一篇雪域高原的荒蕪,沒有陡峭的山坡,只有蒼涼迴旋的寂寞。
無人機拍下風雪,一如阿樂師傅在無人機下降時幫我抓無人機那孩童般的開心歡笑一般,漸漸的顯得不再寒冷。我們三個人就這樣傻傻的守在達木喬埡口旁,卻一直不得見阿尼瑪卿的真顏。
回來後,有朋友問我遺憾嗎?我總是搖頭:其實沒有什麼好遺憾的,轉山的路,就如人生的路,下一秒我們會遇見什麼,我們不知道,我們沒法也沒有時間執著的去守株待兔的等待什麼人出現在我們身邊,沒有時間去等待我們期許的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只能隨著時間流水不斷前行,對與錯都顯得不那麼重要,只要問心無愧,就已足夠。
那一天轉山的路到了最後,路過覺木央拉。
那是一處在藏族人口中的聖地。瑪尼堆的風馬,在漸暗的天色里,也開始瑟瑟發抖。聖地則恰巧躲在了瑪尼堆後,那是一處石壁上的石洞。
阿樂師傅沒有說什麼,從狹窄的石洞鑽了進去,又從另一側的洞口鑽了出來,然後興奮的告訴我們,這個洞,體型不是重要的,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能進出,心帶邪念的人,只能原路退回。
石洞真的很小,只容一人蜷身而過。說真的,進洞的那一刻,真怕自己那仿佛生鏽的韌帶,讓自己卡在洞里,無法穿過,那就尷尬了。卻發現石洞如同有靈一般,滑身進洞出洞,不過一瞬間的事情。
當我和皮亞力都鑽過覺木央拉的石洞,阿樂師傅掩飾不住喜悅:“你們,很好嘛,很好!你們是神山保佑的人。”他依舊憨笑,帶著濃濃的藏腔味的漢語,那笑容仿佛融化了天地,虔誠而友善。也許,人真的需要信仰,需要能讓自己有敬畏之心的信仰,然後一輩子,不斷的在紅塵中修行錘煉,慢慢的不斷、不斷變成更好的自己。
離開覺木央拉不遠,有一條湍急的河水,橫在路中,或許得慶幸,包了阿樂師傅的車。如果按照原本的計劃轉山,在這樣的季節,趟水過河,估計要凍成狗了。好了,這裡提醒下要轉山的各位,這條河,如果在夏季,水流肯定更加湍急,一切註意安全。
過完河,阿尼瑪卿的轉山路就快要結束了,下 大武 的零星燈火,已經依稀可見。我開始不舍,不舍這段沒有“走完”的轉山路,開始不舍阿樂師傅那淳樸的笑容。
回到特丹的家,一壺美酒,一聲問候。在藏族人心裡,轉山是件很神聖的事情,能轉完神山,不管以什麼形式,都是值得慶賀的。喝著酒,吃著羊肉,我開始憧憬,下一座,也是我生命中最後的一座神山尕朵覺悟。
我會遇見誰,又會遇見怎麼樣的事,而更多的也許,是我會遇見更好的自己。
高原的星空
在暗夜裡璀璨
年少時的我們總說
長大後我怕活成自己討厭的模樣
直到長大後才明白
那些曾幾何時討厭的模樣
不過是年少不懂事時單純看待表象的模樣
就像阿尼瑪卿
就像我沒有“走完”的轉山路
是神山教會我放下執著
就像放下曾幾何時我們“討厭”的模樣
尕朵覺悟旁 鮮為人知的所在6歲那年的夏季
格桑遍野
揮別牧場成群的氂牛
磕長頭匍匐前行
懵懂年少的年歲
夏多才仁
讀不懂神山的虔誠
只為尕朵覺悟的信仰
三年前的 玉樹 ,那些純真的笑臉,和那些並不太好的經歷並存。曾經和很多朋友斬釘截鐵的說,我再也不會去 玉樹 了。可命運的輪迴,就像是冥冥中的牽引,又讓我回到 玉樹 。三年前,我放棄曲瑪萊的行程,是因為主辦方不讓轉山。而我總覺得如果讓我到神山腳下,不轉尕朵覺悟,我會百爪撓心的難受,還不如不去。三年後,我和好友皮亞力來到扎多,只為一圓三年前的遺憾。
轉完阿尼瑪卿的第二天,從下 大武 趕到扎多,命運就仿佛交織無法說清的網,讓兩個心中放不下神山的人相遇。下車見到提前聯繫好的夏多才仁,我對他其實並沒有什麼好惡的感覺,仿佛一切平淡得不那麼真實。但很快的,一切變得熱絡,緣起於我詢問住酒店的問題時,夏多說鎮上所有的酒店都沒有衛生間,沒必要浪費那些錢,還是去他家裡住吧。那份實在的熱情,讓我又仿佛每一次回到藏區,每一次遇到的一個個心帶信仰善良淳樸的藏族朋友,這是我熟悉的藏地,這是我喜歡藏區的原因。
夏多的家,如我記憶里的藏居,並不華麗,也不破敗,堂中牛糞燃起的暖意,夾雜著透過窗戶照進的和煦,那抹陽光恰巧撒在一旁靜默無語,凈白不似藏族的女孩臉龐。我不知道那是夏多的妹妹還是誰。而她的一旁,坐著夏多的父親,一位慈祥和善的藏族老人,一個會一些漢語的藏族老人,對於他那種歲數而言,會說漢語,著實讓我驚訝。夏多,則坐在我和皮亞利的對面,溫著甜茶,時不時的給我們斟滿。他的妻子,並不懂漢語,卻在一旁靜靜的聽著,我們與夏多的聊天,偶爾用藏語和夏多說兩句。如若不是窗外的皚皚素裝,屋裡那如若家一般的感覺,我真差點忘了這些日子的 玉樹 ,冬意漸起。
聊了些許時候,我問夏多,除了賽康寺外,扎多還有沒有不為人知的所在。
這麼一個問題,倒讓夏多興奮了起來,告訴我說,有的有的,有一個當地曾經部落建起的石經城。
“那還等什麼,我們現在就去吧!”我壓根沒有征求皮亞力的想法,詢問又像是不容置疑的和夏多說。那一刻,我多少有些失禮。可我總是抵不住小眾的景點又或者說還算不上景點的遺存。
“好的嘛,好的嘛,我也是這樣想的嘛。”夏多倒沒因為我失禮的語氣不快,反而顯得如我一般興奮。二話不說,就去屋外,啟動他剛買的新車,暖車,出發。
我想,如果我沒遇見夏多,我永遠不會知道,在尕朵覺悟神山腳下,有那麼一個歷史久遠到可以追尋到19世紀的石經城。
這個名為邦日朵卡的石經城,應該沒有多少人有聽說過。這一片地區在解放前是邦日丹瑪部落屬地。清朝 咸豐 年間,約1851年至1861年間,竹節活佛圓寂後轉世在 蒙古 爾津族 蒙古 爾津百戶的弟弟昂力拉根成為竹節寺喇嘛,將竹節寺屬及歇武賽巴併為一族,竹節寺竹節族寺、族合一。從此邦日丹瑪部落信奉噶舉派,自邦日丹瑪人青才江開始推行重要法則:對屬民不再用重刑,而是視情節輕重讓違法者鑿刻石經,情節越嚴重鑿刻的石經越多,因為邦日丹瑪部落這奇特的懲罰方式成就了這一片位於尕朵覺悟神山腳下那神秘而鮮為人知的石經城——邦日朵卡。
或許真的需要感謝夏多,高原暖人的陽光和高原稀薄的空氣,一樣讓人有獨特的感覺。而穿行在邦日朵卡,給人的感覺更加獨特。
它比不上嘉納嘛尼石經城的大,也比不上 玉樹 地區那神奇的水瑪尼、冰瑪尼,但它沉澱下來的歷史厚重感,和經文鑿刻間對自己所犯錯誤的深深悔悟,是其他石經城所沒有的。
那是一種說不上來的感覺,就像邦日朵卡,腳下的塵土,和薄薄雪晶,一切都顯得自然的真實,雖然古舊,卻更加舒服而富有禪意。
不時,有轉經的人兒走過,畫面寧靜。
等我飛完航拍,拍完照片,皮亞力已經幫我背起攝影設備,夏多也問我要走了麽。
我笑著擺擺手,說,來了,怎麼都得看看,起碼轉上三圈再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