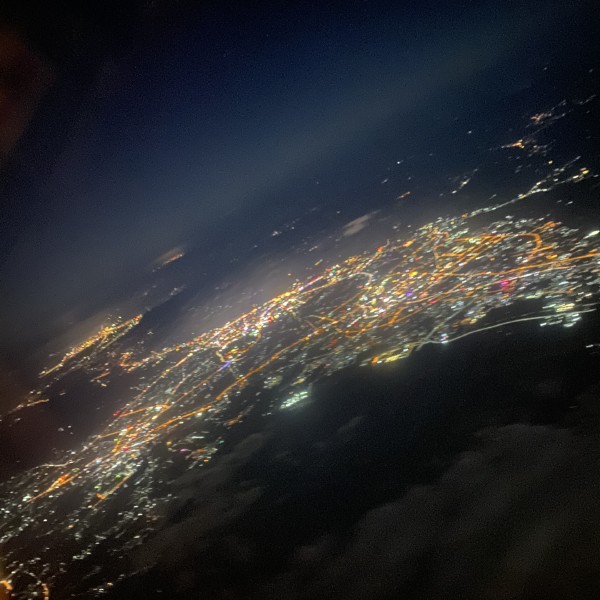24歲世界旅行|摩洛哥篇







組好了駱駝,我們要去沙漠營地。上次騎駱駝八年前了吧,應該是在莫高窟。不知是否撒哈拉更凶險,今天覺得好顛。背著十幾公斤的大包咚咚,每一個駱駝步鐵硬,像一把榔頭把我往水泥地里砸,屁股飛花。我跟一旁micky說:“my backpack makes the camel not very happy”(我的包讓駱駝不開心了)。micky說:“you need to pay double price”(你得付雙倍的錢)。





熾陽走到月清,大漠蒙上幻夢面具。迷濛而妖隱,哪裡聽見狐狸在念經。像一次超現實主義冷抒情,你看到一張明白的畫面,每一筆都看清,可你卻再沒有如此糊塗過了。沙海月,似乎藏著真相,似乎只是廢紙。




抵達營地,燈火沁紅鴨蛋黃,沙漠動了情。白月光流水,沉入沙子,撈一捧黃粱全是月餅味。選好了帳篷,Micky說去沙丘上望望月光清凈。我們熊步爬上去,坐在沙漠的頭髮尖,帳營像打在電影幕布上的茸茸光團,遠處天沙分野,人落在第三個世界。
micky和marie在那邊說著悄悄話。我和南洋哥坐這邊,看著天沉默。一無所有,此刻這是個美妙的詞。南洋哥下午騎駱駝超興奮,他說第一次見沙漠,好美啊!“啊”字用力強調,像霸王指江山。我一想也是, 馬來西亞 除了水就是樹。就算有沙漠,早給熱帶陣雨淋成水池了。白天不懂夜的黑,熱帶不懂沙漠的心事。
這會兒躺在沙子上,馬來哥好像有心事。過了會兒他轉過來說,兄弟,完了。我說咋了?他說,完了。我說咋了?他終於說,我腰包丟了。我說錢卡護照在裡邊?他說是。這一回,輪到我不知道說啥了。他說可能在車上,我只能催他快去聯繫司機,還能救。其實這會兒沙漠也沒信號,他說只能明早見分曉了。他還正了正眼鏡,說哪個姑姑教過他,這種時候要忘記一切,享受當下。




那就享受當下。晚飯又是tajine,座上兩個 波蘭 人神采放飛,講著爬 摩洛哥 最高峰的故事。路如何陡峭,營地如何缺氧,山頂如何極寒。這山叫Toubkal,四千一吧。來的時候我查過資料,太矮了沒必要爬。他倆終於講完山裡的英雄傳奇,問在座其他人行程。我說我 北非 東非 ,然後去 尼泊爾 ,走走EBC環線。他們說哦,你也喜歡戶外運動?我說是的。他們說嘿嘿那你最高到過多少?我說 秘魯 最高峰,六千七吧(見 秘魯 篇)。南美往事飛散,猛地回頭,站在Huascaran的雲場和冰川之上,仍是我所有人生中最震撼的時刻。每一顆用力擲出的沙子都不會白費。
吃了雞,嚮導帶我們找了片清涼沙坐下。生火,擊拳。幾個阿拉伯小哥打著長鼓,唱起飛跳的歌。這是 非洲 大陸傳出的神秘歌聲,鼓點清脆精神。陌生的歌詞,像把木鈴鐺們一顆顆擊向沙漠深處,飛累了,又落水咕咕悶響。火光染人的臉,圓圈外看不清。大漠空茫,風在迷路。天邊居然劈著一根根閃電,沙漠像要撞上大海。有什麼東西扔進黑暗中忘了,有什麼東西,從未如此堅硬。本科的時候,一個夏天傍晚從食堂出來,小果子爛地上,草氣沖鼻。好久沒運動,突然想去操場走走。看見一群 非洲 留學生就坐跑道邊,打著木鼓,唱著另一片大陸的歌。那是我上一次聽見 非洲 的鼓聲,像黑屋子一顆顆飛奔的光團。那時聽黑人兄弟唱著他們的遙遠家鄉,今天穿出時間山洞,我倒成了異鄉人。


非洲 歌鼓

起得很早,在下雨。撒哈拉居然下雨了。想到旅途中那些驚喜。外邊漆黑,風搖樹拍著帳篷,一鞭又一鞭,草原或是森林。micky她們坐越野車去滑沙了,是個付費項目,沒興趣。南洋哥急著回去找腰包。我們就坐著來時的駱駝返回。來時逆著沙漠熱浪,走時糜糜絲絲的雨,薄影子,濕駱駝。


下了駱駝,沙漠嚮導要小費。我給了些,又問南洋哥要。南洋哥說你搜遍我全身汗毛,能找到就是你的,內褲也可以搜。嚮導又攔著堅持了會兒,明白情況就讓他走了。估計內心罵人:你搞丟了錢包,我們跟著倒霉。
上車,滑沙的人提前到了,昨天的座位已坐了人。南洋哥有點怯,我說你快去問啊,他才猶猶豫豫走過去交涉。感謝上帝,那個 法國 人像拎著一隻無路可逃的耗子,從椅子旁的空隙銜出了他的腰包。空隙很淺,於南洋哥卻是無底深淵。走上斷頭臺又宣判無罪,他大口大口說著謝謝謝謝,幾乎有點缺氧。我也鬆了口氣,沒護照沒卡沒錢,我得把全身現金給這個 馬來西亞 華人,都不知能不能救命。


三天團其實只有兩天,最後一天坐車回家。客觀講其實挺沒勁的。景點沒幾個,氣象平庸,沙漠又匆匆而過,就坐了兩趟駱駝。還一堆購物點和十雙討小費的手。隨意吧,看見了撒哈拉,哪怕只有一眼。橄欖樹來去在心中。
我就不回 馬拉喀什 了,直接北上 非斯 (Fes)。換車的時候,荒誕的事情又發生。訂團那天,我已付過去 非斯 的交通費。這會兒司機居然強行要我上另一輛出租,還要我交錢。我說我付過了,這個獃子不聽,像可笑的街頭無賴,你要去菲斯,你就得付錢。我說,我付過了。這句話只有四個字,如此形而下,居然有人聽不懂。一個人自願放棄他的理智,倒車向史前洪荒的爛泥,只會吃肉,多悲哀。
窮途末路,Marie從哪裡突然出現,像引人飛升的天使。她們也去 非斯 ,那天在 馬拉喀什 還一起訂的。其實我們的麵包車就在旁邊。我立馬忘了眼前這個敗壞的人,和marie上了人生中正確的車。
南洋哥回 馬拉喀什 ,就說再見了。下回別隻記得拍照,也留心下續命糧草。我們的車七個小時開 非斯 。中午餐廳休息時,micky突然說她病了。我說物理上的?有點搞不清是真不舒服,還是旅程將盡,撒哈拉鄉愁的玩笑話。
她是真病了,可能冷冷熱熱犯了感冒。午飯也沒吃,中間幾次廁所商店休息,她根本不下車。我們買了點糖水,她喝了幾口充充能量。我說我也經常生病,問題不大,只是需要時間。
三天旅程,的確要結束了。汽車在最後的跑道上衝刺,窗外是乾黃的草草山山。不想下車又等待下車。夜路還是太多了,遇到的人和事像不小心翻開的紙牌光彩,綻開在一個小角落,淺淺的煙火幾朵。我會想起我的朋友們。


抒情太早了點。汽車七點到 非斯 ,Micky很不舒服了走不了路。我訂的青旅近,三分鐘, 七美 刀。她們跟著我去了這個好去處。放了東西,又出門小逛熱閃閃長街。好窄好多人,想起小時候公園玩的碰碰車頭暈。坐進一個路邊攤,我和Marie吃著 摩洛哥 大肉麵包,Micky和一旁的 摩洛哥 小哥討論過去的旅行,工藝品店的反光紅橙黃綠。突然下起暴雨,一千零一夜青年三,晚上造個夢大飛毯老樹精快顯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