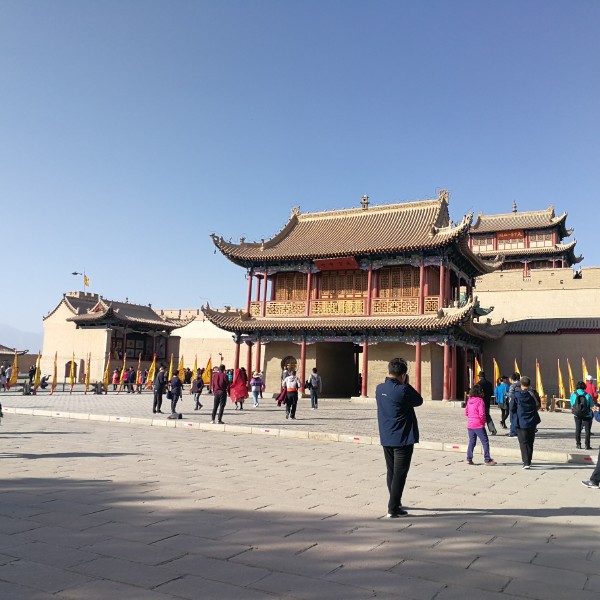28天橫跨印尼,坐著摩托去火山,乘著小船去看“龍”!(附印尼小眾目的地全攻略)

老吳不禁回想起自己出發前在地圖上劃的一段段連線,找到的當地旅行社的聯繫方式,他感到身體里有一種可以被稱之為叛逆的情緒在蔓延,然後不停地衝擊著名為“傳統”與“安全”的枷鎖。這份情緒使他幻想起自己獨立征服這段旅程後的樣子,於是那份虛榮像盔甲一樣被覆在“叛逆”之上,讓發出的衝擊更為有力。
可惜的是,直到老吳筋疲力盡的走進旅店大廳,這氣勢洶洶的衝擊仍沒有衝破堅固牢靠的枷鎖,最後只得讓這股衝動如浪潮席卷高地後的水窪一般在溫暖舒適的床上消磨殆盡。

踏上從市中心去往機場的快軌,便意味著離“選擇”更近一步。舒適總能讓人感到安逸,安逸總會讓人想要放棄。經過一晚的時間,老吳想要衝破這層枷鎖的決心像出水的魚,頭尾不停在地上拍動可卻怎麼也掙扎不起。最後,老吳決定了去往最終目的地——布羅莫、伊真火山的方式——還是和計劃一樣,跟隨旅行團一起。
這樣,老吳便可以不帶任何顧慮地前往 日惹 ,然後輕鬆地跟著旅行團完成這次旅行。對於這種旅行方式,老吳駕輕就熟。精力本就比金錢更有價值,而將金錢花費在減少精力上,又有何不可呢?至於途中可能被忽略的景色,與目的地的景色相比,也就無足輕重了。
決定了這件事,前一天內心掀起的波瀾也就漸漸平息。鐵道列車在繁華的都市與原始的郊野之間飛馳,老吳漫無目的的悵望著窗外,看著一道道轉瞬即逝的風景。空曠的田野上,突然闖出一個騎著單車的女孩,她雙手緊握著車把,俯著身,腦袋幾乎快伸到了車把手的位置,長長的馬尾辮像黑絲帶一樣在空中飄揚,她像是在追趕什麼,可是眼前除了幾棵芭蕉樹再無其他。
緊跟在女孩身後的,是一個個子矮些的小男孩,從他的姿勢不難看出他已經筋疲力盡,想要超越前面的女孩兒但又對年齡造成的差距無可奈何,他只好大張著嘴,要求她慢一點,可女孩卻絲毫沒有理會,只是高舉起自己的左手,背對著男孩,帶著些許挑釁和調皮的意味擺動起來,然後單手扶著車把,在田埂間一邊笑著一邊歪歪斜斜的繼續追趕著什麼。
幾秒鐘後,這對姐弟便消失在老吳的視野中,接著,列車駛 上高 架橋,周圍的景緻也從田野變成了正在施工的高速公路,在這段還沒有淋上瀝青的路面上,三個孩子的出現再次打斷了老吳的思緒。他們一個個都赤著小腳,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無憂無慮的踢著裹滿了泥巴的皮球,陣風吹過,揚起了孩子腳下發紅的塵土,卻無法掩蓋他們臉上最簡單純粹的快樂。後來老吳告訴我,那一刻他突然再次心緒激蕩,明白了那個田野里的小女孩在追逐什麼,“她在追逐風。”他說。
不長的車程,把這座城市的繁盛興衰演繹的淋漓盡致,是都市圈的忙碌與繁華,是芭蕉樹下勤勞的人家,是田野里逐風的孩子,也是鐵軌旁耐著性子等待過街的摩托大軍。貧窮與富有,欲望與純粹,在這裡被雜糅為一談,或許只有被賦予了“浪漫”與“冒險”精神的勇士,才能走出泥沼,找到未來的路。

老太的第一次搭話大概是為了確認時間,她有些害羞的碰了碰老吳,嘴裡含糊著老吳聽不懂的當地語言,手指著老吳手中的手機,又比了比自己的手腕,老吳明白過來,打開手機給她看。她先是定了定,似乎被手機屏幕上繁雜的圖案和“怪異”的文字弄得暈頭轉向,然後又凝起眉仔細瞅了瞅,直到老吳指了指屏幕上方的幾個阿拉伯數字,她的眉宇才逐漸伸展開來,嘴角也浮現出一縷笑,伴隨著豎起的大拇指和合十的雙手錶達著感謝。
當某些人離開我們時,我們總會以一個動作、一個表情記住他們的存在,然後謹慎地將他們珍存在記憶最深處。此時此刻,這個坐在老吳身旁的老太的一個微笑,像觸發了老吳心中洪閘的開關,一股無端的悲傷從老吳心底猛地涌出,夾雜著先前被禁錮起來的“浪漫”與“冒險”,迅速彌散在老吳的整個身體。緊接著,飛機引擎的轟鳴聲在跑道上空迴響,機身頃刻間向上傾斜,伴隨著一陣短暫的眩暈,一股沉重的失重感如巨石般壓在了老吳的心底,重到幾乎把本就瘠薄的靈魂榨乾。老吳瞥了瞥一旁的老太,她眯著雙眼,嘴裡一直念著什麼,念得安靜,念得 平和 ,就連機艙內巨大的引擎聲,都漸漸沒有了聲響。
老太轉過頭,好像也看到了老吳有些污濁卻噙滿淚水的雙眼,於是她將身子湊過來,臉上最開始的羞怯還沒有完全褪去,主動搭話似的低聲問老吳從哪裡來。老吳回答她,她似懂非懂的點了點頭,然後看向一旁的老伴,嘴裡好像說著些什麼,還沒等老吳反應過來,一隻飽經滄桑卻溫暖無比的手已經輕輕搭在老吳的肩上,緩緩的拍了拍。
晚風漸息,皎月漸隱, 日惹 夜晚的空氣中好像多了某種東西。某種讓人感到靜謐的特殊的氛圍,仿佛氣味般悄無聲息的在空氣中蔓延,它飄向熱鬧的城市、繁華的街道,也飄向落寞的小巷、無人的山林,它甚至安撫了老吳捲起狂瀾的心潮,在一片夜色下,為他帶來撩人的困倦,送他進入夢鄉。



風輕輕搖晃著黃白花朵的雞蛋花樹,似乎要將緩緩飄落的雞蛋花當禮物送給披著藤衣的水池姑娘,水池姑娘欣然接受了,她將散落著的雞蛋花依次排列開來,然後害羞的別在自己通紅的耳畔,發出淺淺的“嘩啦嘩啦”的笑聲。


老吳真正前往 婆羅浮屠 已經是驕陽當空的時候了。經過了一個早上的精心收拾,老吳刻意掩飾住那幅皮囊上略顯出來的黯然,讓它再次放出光彩。從青旅出發到 婆羅浮屠 是一段不近的路程,一路上,一切風景都像是被炙熱的太陽在不經意間烤的褪了色,天空是淡淡的藍色,雲是淡淡的白色,路的盡頭是淡淡的灰色。那是一種難以形容的不經意,仿佛是被什麼人隨手擺弄了一番就丟到一旁的玩具,袒露著胸膛,浮出一絲與老吳心境全然不符的豁達和隨性。
婆羅浮屠 的入口處,成群的游客扎堆擠在檢票的閘機前,聒噪的言語聲在本就酷熱的空氣中逐漸升溫,最終演變成一種嘈雜的、毫無秩序的喧鬧。距離閘機數米之遙的景區內,埋伏著一個又一個雙眼放光的“掠食者”,他們緊緊盯著那些三兩結伴或是獨行進入景區的游客,在他們眼中,這些人就像是大草原中離群的食草動物,是可以讓他們飽餐一頓的絕佳對象。他們耐心的等待獵物慢慢步入狩獵範圍,然後靜悄悄地跟在身後,等獵物終於發出對方向、觀賞順序等等的疑問時,他們便藉著“導游”的名號一口撲上去,緊緊咬住獵物的屁股不鬆口,直至獵物難以忍受高溫下他們發起的猛烈攻勢而投降時,他們才露出“掠食者”專屬的充滿尊嚴的笑容。當然,這些所謂的“掠食者”中,也有一些溫良的存在,只是在辨識上是個難題罷了。
老吳並沒有受到這些“掠食者”們的侵襲,因為對於他來說,“打卡”便是此行的全部,而這片草原上沒有任何他想攝取的養分,他只是跟著群體匆匆的來匆匆的去,自然不會讓掠食者們抓到機會。
陽光絲毫沒有減弱的勢頭,偶爾幾朵迷路的雲彩遮住太陽,讓陰影下的游客暢快的簡直要為之歡呼。等太陽再次露出頭來,人們便紛紛撐開自己花哨的遮陽傘,或是帶上邊檐寬平的草帽,又或披上顏色艷麗的頭巾,以求將來讓自己黑色捲翹的睫毛在明麗肌膚的襯托下更加耀眼。就這樣,這座埋藏在火山灰中的千年斑駁古跡好似一條正被清流穿過的枯幹河床,被點綴上了一片生機。



就這樣,在下一個分岔路口時,老吳沒有兀自向前,而是轉向了一旁的 通道 ,在這片古跡中漫無目的的暢游。遠處看,在層層堆疊的塔壁上,落座著數百尊佛像,它們大都微閉雙眼,交叉盤著雙腿,雙手結著因方向而有著微妙不同的印相。近處看,石壁上又雕著各不相同的圖案,老吳不明白其中的深意,但仍能依稀感覺出壁畫像是記錄著那些發生在千年之前的故事。







太陽已經熾熱難耐,陽光在塔頂和近處的叢林中散落開來。抬起頭進入眼帘的是 爪哇島 上充滿生機與神秘色彩的雨林,低下頭看到的是幾座淡然端坐在蓮花之上的佛像。可老吳臉上卻總是浮現出一絲與之相反的焦躁,他急躁的環繞著塔頂尋找最好的角度,不耐煩的等待著穿著花哨的游客走出取景器,嘴裡還不忘嘟囔著抱怨天氣的炎熱。千年的佛塔屹立不倒,眼前的游客川流不停。老吳嘆了口氣,隨即把視線挪出取景框環視四周,然後在角落尋得一處能夠遮蔽住半身的蔭涼,輕輕的靠了上去。相機被他掛在了滿是汗珠的脖子上,鏡頭自然而然的垂到下腹,在見識了灼人的烈日和紛擾的游客後,老吳對“打卡景點”這種方式產生了一種厭惡,這種厭惡沒有特定的來源,但又確確實實的建立了起來。
老吳回想起門口閘機處的“導游”們,此時,在悠悠歷史長河上,他們似乎一轉而為撐著竹竿的朴素船夫,吆喝著河岸想要渡河的人,他們臉上不再有狡猾的笑容,他們雖然收取報酬,卻能讓想要渡河的人避開時間製造的漩渦,然後一邊欣然觀察著歷史的深度,一邊安然抵岸。到最後,老吳已經分不清他們到底是陰影處等待獵物的野獸,還是帶著善意的朋友,但是老吳知道的是,自己無疑是那個在岸邊踟躕不前的人。
悶熱的微風掠過老吳粘膩的面頰,整片叢林在他身後被擠成一團,緊接著,他想起曾經看到的一句話:“今晨,我坐在窗前,世界就如一個過客,稍歇片刻,向我點點頭,便走了。”






晌午的陽光透過樹葉慵懶的打在泛著漣漪的池面上,黑色的瓷磚則為前廳蒙上了一層清凈。眼前的院子里,老吳遠遠看到一個人正躺在懶人沙發上沐浴著陽光,卡其色的短袖襯衫配著咖啡色的短褲,裸露在外的皮膚上擠滿了各式各樣的紋身,金黃色充滿流浪感的鬈髮不長不短的垂在脖頸處,端正的面孔,高挑的鼻梁和及其壯碩勻稱的體格則散髮出一種吸引人的特殊氣質,讓人忍不住發自內心的贊嘆。他懷裡揣著一本旅店專門為游客定製的出行手冊,然後一條腿交叉盤在另一條腿下麵,半開半閉的雙眼散髮著倦意。
前廳的清涼帶著一絲不合時宜的寒意迎接著這位烈日下歸來的旅客,老吳提了提嗓子,深深吸了一口氣,嘴巴發出“嘶嘶”的聲音。陽光下的陌生人似乎被這微弱的嘶嘶聲驚醒,睜開略帶惺忪的雙眼,皺著眉看了看這個額頭上髮絲因出汗而結成縷的歸來者。兩人相互對視了一秒,然後各自舉手向眼前的陌生人打起招呼,老吳帶著一絲靦腆,陌生人則帶著一股好奇。
洗去一身的汗味,老吳由內而外感受到新生般的愉悅。午後的陽光總是有一種魔力,像晚燈吸引飛蛾那樣吸引著那些心情愉悅的人前去享受。老吳抵擋不住這種誘惑,他的雙腳幾乎不受控制的就走向了陽光下的另一張懶人沙發,然後重重的坐下去,伸了一個幅度有些誇張的懶腰。坐在一旁的陌生人率先搭起了話。他首先贊嘆了一番爪哇充沛明媚的陽光,語氣中帶著真誠與想要交流的渴望,接著他又說起自己生活的城市是如何的陰霾,然後他將話鋒突然轉向 爪哇島 的美食,最後他甚至介紹起了自己身上紋身的來歷。就這樣,一來二去的對話中,兩人逐漸熟悉起來。
陌生人名叫肖恩,從 倫敦 來,從事一份輕鬆且自由的工作,他的旅行經歷遠比老吳豐富,在澳洲觀星,在 埃及 潛水,也在 北歐 尋鯨,這次正值假期,他來到這裡想要穿越 爪哇島 ,計劃從 日惹 開始,到 巴釐島 結束。肖恩似乎很喜歡這個典型的東方人,除了覺得他的木訥和骨子裡的靦腆很有趣,更感覺到他的言行中帶著一種真誠。巧合的是,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地—— 布羅莫火山 和伊真火山,雖然兩人前往那裡的方式不盡相同,但這似乎並不影響他們利用這個話題來延展對話的寬度,最後,肖恩甚至直接乾脆的提出邀請,希望老吳能和他一起去逛逛這個小城。
老吳沒有拒絕肖恩的邀請,因為他從肖恩身上發現了一種魅力,一種沉穩、自若、踏實和可靠從他的言行中散髮出來。然而,對於老吳來說,肖恩卻是用一種在他看來有些瘋狂的方式來瞭解這個城市——騎摩托。 雅加達 的“兩腳獸”大軍仍歷歷在目,而現在老吳卻即將成為他們當中的一份子,在凝滯的車流中穿行。
摩托是被兩個極其友善的當地人送來的,在知道老吳完全不會駕駛摩托車後,他們先是有些吃驚的笑了笑,然後毅然當起了他的教練,要知道,在這裡騎摩托這件事對於十二歲的孩子都是輕車熟路。“補習班”沒有耽誤太多時間,甚至連當空的太陽都沒怎麼挪動。臨出發前,兩位友善的老師仍放不下老吳這位看上去有些膽怯的學生,只好留下自己的號碼,再三叮囑兩人一旦出現情況就立即聯繫他們。
最後,肖恩還是有些不放心地關心道:“沒問題吧?”
老吳開玩笑似的點了點頭:“沒事的,這不是還有你一起嘛?記得等等我就行了。”

時間隨著車輪的轉動飛逝,原本紋絲不動的白晝也逐漸起了變化。大街上的人聲逐漸嘈雜起來,原本躺在民居水泥地板上睡覺的婦女們點燃了家中的竈台,伴著悅耳的歡笑聲,孩子們穿著校服的身影也隨之出現,還有不知道從哪裡涌出來的“兩腳獸”大軍,幾乎要將老吳與肖恩吞噬。位於小城中心的 馬裡 奧波羅大街,更是展現出了不一樣的活力。大型商場、國有旅行社、銀行、餐廳、紀念品店鱗次櫛比,馬匹精壯裝潢精緻的四輪馬車、乘客在前車夫在後的傳統三輪車、隨處可見的摩托車、各國游客、各色小販、警察、乞丐、流浪貓,互不干擾的生活在這條寬敞卻擁擠的街道,他們無限延伸著 馬裡 奧波羅大街的維度,即使晚霞褪去夜幕降臨,他們也能讓自己生存的地方經得起時間洪流的沖刷,使它如尼羅河般流淌不息。



經過半天的相處,老吳與肖恩逐漸變得默契起來,兩人伴著如洗的月光,落座在小院吧台前的長腿凳上,這次是老吳先開了口。
“明天有什麼打算?”老吳的手中正搖晃著一杯由沖劑製成的奶茶。
“我在旅游手冊上看到了一個洞穴。”肖恩匝了咂嘴巴,放下冰鎮的灌裝啤酒問道:“想不想一起去看看?”
“洞穴?”老吳放下手中浮著一層泡沫的杯子,有些吃驚的轉頭看著肖恩。
“對,洞穴!”肖恩似乎迫不及待想與老吳一同前往,臉上顯露出了巨大的期待,接著說道:“冊子上寫著那裡有六十米高的吊索,有覆滿泥漿的石頭,還有一束來自天堂的光...”
月色下,老吳的瞳孔散髮著細瑣的光芒,顯然,白天由速度激蕩起的冒險精神還遲遲沒有消散。老吳沉下了頭,手裡繼續搖晃著漂著一層浮沫的杯子:“或許在這裡4天時間確實有些 富裕 了,即使明天去了也還剩一天可以用來修整。對!反正厭倦了打卡,倒不如去試試。”老吳這麼想著,隨即,他像做出了什麼決定似的鄭重地抬起頭,詢問了例如支出、時間、人數等等各方面細節,以確保第二天的“冒險”能在自己的控制範圍內。
在兩個人默契地準備各自回屋休息時,肖恩問了老吳的名字。
“你可以叫我Wu,在我的語言中,它還有‘什麼都沒有’的意思。”老吳如是答道。
不同的語言代表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又懷揣著不同的心情。肖恩對這個解釋充滿了好奇,可當他再想開口時,卻發現老吳已經消失在庭院的夜色中了。 中岜朗天坑丨庭院樹影清晨的天空總是蒙著一層灰暗,一呼一吸間還能感受到空氣中浸透的涼意。老吳揉著睡眼,換上了為防萬一而準備的運動短褲,白色的帽子壓住了一頭蓬鬆的像雞窩一樣的頭髮,推開門,發現肖恩正坐在餐桌前的長椅上享用著早餐。
城市到洞穴之間的路並不平坦,或者說,如果不是洞穴的發現,兩者之間可能根本無路可走。汽車行駛的很慢,車輪深軋在鬆軟的土地上,讓本就上下顛簸的車廂發出嘎吱嘎吱的呻吟聲,排氣管噴著熱氣,引擎發出的轟鳴聲同馬匹發出的響鼻聲一樣響亮。天已經亮了,可老吳卻渾然不知,因為他正靠著車窗,自顧自地在夢境中遨游。過了一會兒,肖恩叫醒了沉睡的老吳,示意他目的地已經到了。
渾濁的 日光 穿過厚厚的雲層,幾棵枝葉稀疏的小樹在貧瘠的土地延展開來,沒有洞穴也沒有覆滿泥漿的石頭,更別說那有些誇張的“來自天堂的光”,在老吳面前的,只有一個四周沒有圍擋的大廳,幾排無人的座椅,一個陳舊的舞臺便是全部。老吳是有些失望的,不僅是眼前的清廖,更是因為頭頂被雲層覆蓋著的天空。
大約過了一個小時,大廳熱鬧起來了,放眼過去,皆是老吳熟悉的黃皮膚黑頭髮,不免也有幾個其他膚色的人,在人群中顯得有些孤單。肖恩有些激動地環顧著四周,老吳則不自覺的靠在了椅背上,心裡只覺得一陣陣踏實。一縷陽光在雲層最薄的地方鑽了個窟窿,俏皮地探出頭來,緊接著,雲層終於抵擋不住太陽強烈的攻勢,不舍地把藍天還給了大地。然後一個當地人從大廳後面鑽了出來,點齊人數,示意所有人跟著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