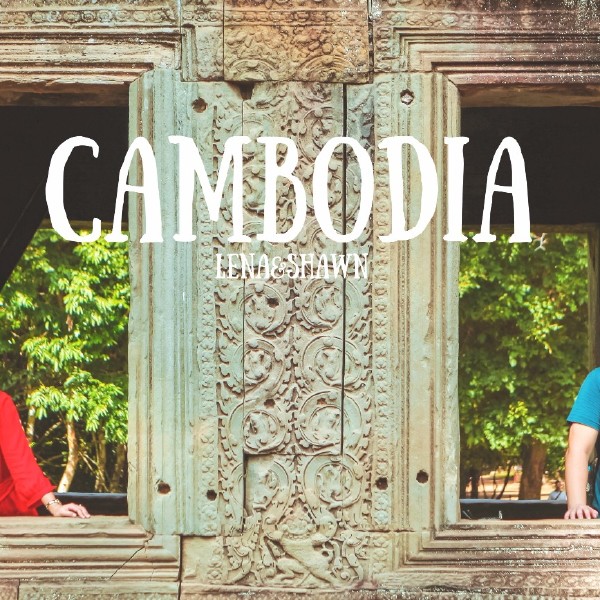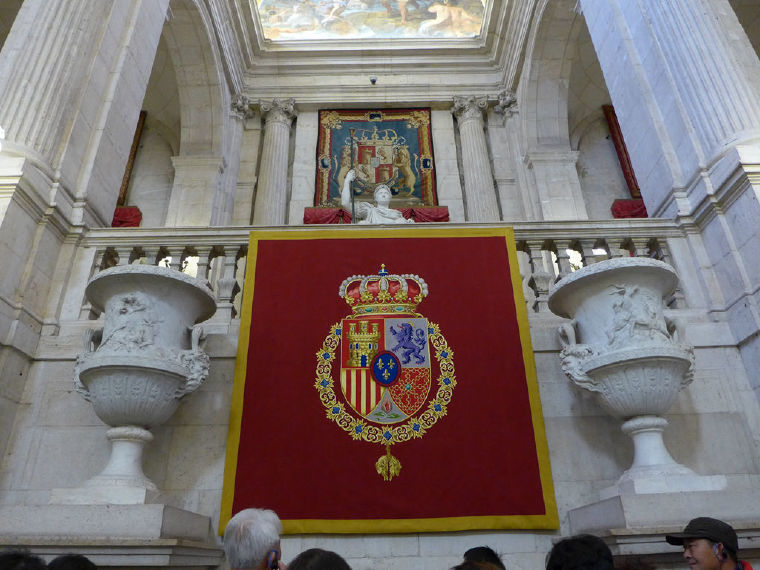西班牙巡禮2: 馬德里的藝術之旅

連環畫式的宗教畫是有著悠久歷史的。早年教堂里的壁畫都呈現出連環畫的形式,天使報喜,耶穌誕生,博士來拜,直到最後耶穌受難。其實這些都是傳播基督精神,教化信徒的重要手段;因為那個時候許多信徒還不識字,與其給他們看《聖經》,不如讓他們看壁畫。所以中世紀的繪畫以宗教題材為主,場景也以教堂為主,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的。

聖母半側而微微下傾的臉龐,安詳的神情,淡淡的甜美笑容,是拉斐爾聖母的“標配”。拉斐爾並不想表現《聖經》中的某些經典情節,而是始終在力圖把母親那份神聖而深沉的愛通過平淡的方式表達出來。


畫面描述了這樣一個瞬間:抹大拉的 瑪利亞 正憂傷地在墓地里尋找著耶穌的屍體,突然發現在她面前是剛剛複活了的耶穌。她緊張而激動地癱倒在地上。遠處的曙光象徵著新紀元的開始。

或許是因為 西班牙 王室從十六世紀才開始大規模收藏 歐洲 繪畫,所以在 普拉 多美術館里看不到 意大利 文藝復興早期的畫如喬托、波提切利等人的作品,而中期三傑中也只看到拉斐爾的作品;倒是晚期畫家的作品有不少。
提香(1488-1576)是文藝復興晚期的 威尼斯 畫派的主要代表,也是查理五世最喜歡的畫家之一;而 西班牙 王室的大規模收藏正是從這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國王開始的。這幅《酒神的狂歡》(1518-21)是提香的酒神系列畫中的一幅,色彩鮮艷,筆觸細膩。在畫面中,有縱情狂歡的,有酩酊大醉的,還有醉眼朦朧的真情流露;這些都標志著,在文藝復興後期,繪畫越來越在宗教的名義下表現世俗的歡樂和感官上的歡愉。

雖然都是宗教題材,可這兩幅畫的作畫時間相差三十五年。前面那幅畫是提香在30歲時作的,顯然那時他對於世俗的放縱和尋歡作樂是持欣賞的態度;而後面這幅則帶有很強的宿命心態。即便美麗聰慧如維納斯,也救不了愛人的生命;烏雲密佈的天空,一旁磕睡著的丘比特,都增添了那份無可奈何的氣氛。

十六世紀上半期,是 西班牙 蒸蒸日上的時期。一個遠在數千里之外的 意大利 公國的總督,居然是由 西班牙 國王查理五世任命的!這個時候, 西班牙 的實際控制疆域北到 德國 ,東到 意大利 ,西到 南美洲 ,簡直是個日不落帝國!

咋一看,這位騎在馬上的神聖 羅馬 帝國皇帝兼 西班牙 國王並沒有如不少騎士像那樣,表現出趾高氣揚,躊躇滿志的樣子。這並不是畫家的表現力不夠,而是捕捉到了人物的真實心態。當時查理五世竭盡全力在米爾貝格海岸打敗了 德國 新教徒,但是後面形勢依然很嚴峻。所以畫家表達的人物不是勝利的喜悅,而是面對嚴峻未來的堅韌意志。據說在戰役的關鍵時刻,查理五世重症在身,是躺在擔架上的前線。
在作這幅畫時,畫家與皇帝已經是十多年的私交好友了。查理五世在三十多歲時就與提香成為好友,把這位 意大利 畫家任命為宮廷畫家,並封為伯爵。據說有一次查理五世來到提香的畫室,彎腰為他拾起掉在地上的畫筆。提香恭敬地說:“我不值得你為我撿起一隻畫筆。”而查理五世則風趣地對他說:“世上最偉大的皇帝凱撒都應該服侍你。”

年輕纖瘦的王子(畫中的他應該還沒繼位)一身戎裝,正準備戴上華麗的頭盔。這似乎在預示著菲利普二世要繼續在查理五世武力控制 歐洲 的道路上走下去,而這條道路充滿艱難坎坷。


這幅《約瑟與波提乏的妻子》(1555)就是丁托列托的作品。這是《聖經》中的一個悲催的故事:波提乏是 埃及 法老的衛隊長;他的妻子看中了僕人約瑟,百般勾引不成,反而把拉扯中奪取的斗篷作為證物,誣告約瑟企圖不軌,將其投入監獄。
圍繞這個故事的畫作有不少;這也不是丁托列托最具代表的作品。不過從這幅畫中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畫家的表現特點:畫面充滿幻想,人物動作誇張,戲劇性效果很強。這是畫家的追求,一是反古典,二是優美雅緻。

這幅《摩西獲救出水》(1580)是維羅內塞晚年的創作。摩西是猶太教的創始人,最偉大的先知;相當於佛教中的釋迦牟尼。當初 埃及 法老獲得靈感,得知有個先知降生,日後會造反,於是到處搜捕新生兒。摩西的母親不得已把他放進一隻箱子,藏在尼羅河畔的蘆葦叢中。後來法老的女兒去河邊洗澡,發現了摩西,就把他收養起來。
這幅畫便是表達了發現摩西的瞬間。一個侍女抱著不知危險的小摩西,另一個侍女在向公主解釋著情況;而公主正在猶豫,如何處理這個從天而降的嬰兒。


魯本斯多才多藝,活躍於藝術與政治之間。他不僅是那個時代最著名的畫家,還曾作為 西班牙 國王的使節,在外交上斡旋,並 成功 為 西班牙 與 英國 締結友好關係,因此而封爵。
魯本斯的作品色彩濃重,氣氛熱烈。這幅《愛之園》(1630)是他在53歲時的作品,紀念他自己在那年迎娶了16歲的妙齡少女 海倫 !畫面左側在翩翩起舞的正是這對新婚夫婦,而天上人間都在為之慶賀。

這組畫都收藏在 普拉 多美術館。魯本斯負責畫面的整體佈局以及繪製代表感官體驗的人物,而老揚·布呂赫爾則以他的精湛技藝展示出各種能創造出感覺的物體和元素。
在畫面中,一位 豐潤 的少女是人類味覺體驗的代表,滿滿一桌美味佳餚,就像 中國 皇宮裡的“食前方丈”;旁邊森林之神還在殷勤勸酒。桌子周圍擺滿了格式各樣的野味、獵物、水果和魚類;遠處的背景中還有各種家禽。魯本斯營造瞭如此豐富多彩的味覺空間,設計了一個如此巴 洛克 的場景;而老揚·布呂赫爾則把不同材質的食物表現得惟妙惟肖,每件物品,每個細節都表達得那麼栩栩如生。兩人的珠聯璧合成為藝術史上的一段佳話。

表現大衛與歌利亞的作品多如牛毛;最著名的當然要數米開朗基羅的《大衛》雕像,那是表現用拋石機襲擊歌利亞之前的大衛,沉著冷靜。其實米氏的《大衛》之所以如此受推崇,當年 佛羅倫薩 政府為此專門要成立一個包含達· 芬奇 在內的委員會來決定將這尊傑作安放在哪裡,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這尊雕像重現了古 羅馬 標準的美男子形象!而之前和之後大部分畫作和雕塑表現的都是擊敗歌利亞之後的大衛,一副躊躇滿志的樣子,因為畢竟他後來當了四十年的 以色列 王。
可是 卡拉 瓦喬並沒有套用上述兩種表達,而是選擇了一個有些血腥的場景:大衛擊倒歌利亞之後,正在割下他的頭顱!月光下的大衛孤獨沉默,一雙手堅定地忙碌著。可以想象,這時整個戰場都鴉雀無聲,一片死亡般寂靜;無數雙眼睛與月亮一起註視著年輕的大衛!而 卡拉 瓦喬用高超的明暗對照,將觀眾的全部註意力都聚焦在人物戲劇性動作上,聚焦在大衛手臂和腿部的肌肉上!
說句藝術評論家們都不願意說的話, 卡拉 瓦喬用這樣血腥的場景表達大衛的故事或許還有一層原因,就是畫家本人有一定的暴力傾向!雖然他一生只活了不到四十年,可卻屢屢爭鬥而聲名狼藉,據說他的治安記錄和審訊記錄可以足足抄錄好幾頁。所以他的作品中常常表現一些暴力的鬥爭、奇異的斬首、拷打和死亡等有血腥的場景。當然,即便如此,他依然是那個時代一位傑出的畫家。

古典主義講是非,分正邪。所以古典主義繪畫都是有點兒端著的。你看普桑這幅《勝利的大衛》(1630),勝利女神手持花環獻給大衛,一群小天使也在一旁載歌載舞地慶祝,而勝利後的大衛並沒有喜氣洋洋,躊躇滿志,而是傷感地凝視著歌利亞被斬下的頭顱和巨大的盔甲。

關於這幅畫所演繹的故事有好幾個版本,至今沒人能說明白這位美女代表誰;只是人們發現她與畫家妻子長得很像。但是畫法的精湛和用光的技巧與倫勃朗以往的作品一脈相承;讓人想起那幅著名的《夜巡》。

如果說, 西班牙 最偉大的作家是 塞萬提斯 ,那麼最偉大的畫家就是委拉斯開茲。委拉斯開茲(1599-1660)深得菲利普四世的喜愛。據說這位菲利普二世(見前面提香的畫)的孫子看了畫家為他所畫的肖像之後十分滿意(不知道是否就是這幅),竟下令在宮中取下自己的所有其他畫像,並規定今後只允許委拉斯開茲為自己畫像。

畫面描繪了這樣一個瞬間:太陽神阿波羅去火與工匠之神伏爾甘的鍛造廠,向他揭露他的妻子,愛神維納斯與戰神馬爾斯之間有私情。(咳,這是何必呢,四個人,不,是四位神都屬於 羅馬 十二主神;大家在一個萬神殿里待著,低頭不見抬頭見的!)聽到這個消息,火神與他的同事們驚愕不已;他們正在為戰神打造兵器呢!
這是委拉斯開茲少有的幾幅以神話為題材的作品。如果沒有太陽神頭上的陽光燦爛,這就是一幅生動的世俗畫,匠人們臉上的憤怒和驚訝,以及遠處那位匠人那帶有幸災樂禍的表情,還有他們渾身發達的肌肉,都遠遠超出神話的範疇,讓人身臨其境,感同身受。

1625年,由斯皮 諾拉 侯爵指揮的 西班牙 軍隊對 荷蘭 戰略要地布列達要塞圍困 成功 ,迫使 荷蘭 軍隊投降,使 西班牙 徹底征服了 荷蘭 ,這使得 西班牙 的勢力進一步向北擴張。畫面表達了侯爵受降的場面:遠處的要塞上空還飄蕩著戰火硝煙, 荷蘭 指揮官謙卑地向侯爵遞交了城市的鑰匙。

在我看來,《宮娥》(1656)最大的特點就是像一幅照片。用對畫家贊美的語言來講,就是其魅力來源於整個場景及其每一個細節的瞬間真實感。似乎在畫面的前方有一聲呼喚,所有人,從小女孩瑪格麗塔,到公主的隨從包括那個侏儒,以及正在作畫的畫家本人,他們的視線都投向一個方向!是哪裡呢?畫面左後方的鏡子揭開了謎底:菲利普四世和王后正站在畫面以外,擺著pose讓畫家在畫肖像呢!如果那個年代有照相機的話,不過是“卡擦”一聲的事情;可對於一位畫家而言則是一項巨大的挑戰。
首先要構思這樣的場景來作畫就是一個巨大創新。其次是要捕捉每個人的瞬間表情。最後還得讓光線匹配,表情協調。於是就成為了名畫家的名作。

在維拉斯開茲的家鄉 西班牙 南部的 塞維利亞 ,有一尊畫家的雕像,基座上寫著:紀念真實的畫家。

戈雅出身貧窮,從小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因具有繪畫天賦而在二十多歲脫穎而出。戈雅一生在畫壇勤奮耕耘,不斷探索,所以畫風多變。下麵這幅《陽傘》(1777)是他在三十歲上的作品,帶有明顯的洛可可式風格,同時還有 西班牙 特有的東方文化氣息。


當然,這兩幅別出心裁的組畫在當時還是引起了巨大震動。女主人公是誰?訂購者又是誰?兩幅畫哪幅在先,哪幅在後?最重要的,畫家創造這兩幅畫的真正含義究竟是什麼?兩百多年過去了,這些問題至今依舊懸而未決。

作為宮廷畫師,戈雅在創作這幅《 卡洛 斯四世一家》時顯然投入了自己的情感,所以咋一看國王一家衣冠楚楚,其樂融融;仔細看去,卻一個個表情獃板,虛弱無力,簡直像一群行屍走肉。這種明褒暗貶的手法體現了畫家高超的繪畫技巧。或許是效仿維拉斯凱茲的《宮娥》,戈雅把自己放在了左側的陰影里。

六年後,戈雅請求攝政院讓他將這一事件用畫布展現出來。於是就有我們看到的下麵兩幅戈雅的傑作。《1808年5月2日》(1814)描繪了 馬德里 市民與 法國 占領軍搏鬥的情景:法軍全副武裝,由拿破侖的龍騎兵和 埃及 雇佣軍組成;而 馬德里 市民缺乏裝備,有的只是捍衛自己家園的勇氣。畫面著力表達了搏鬥的殘酷場面。

畫面中,近景中一片屍體,幾個修士和百姓正在被執行槍決,而不遠處又押來了一隊犯人……腳下血流成河,遠處天色陰沉。畫家把光線集中到穿白襯衣的死刑犯身上:憤怒的臉,張開的雙臂,就像基督臨上十字架時的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