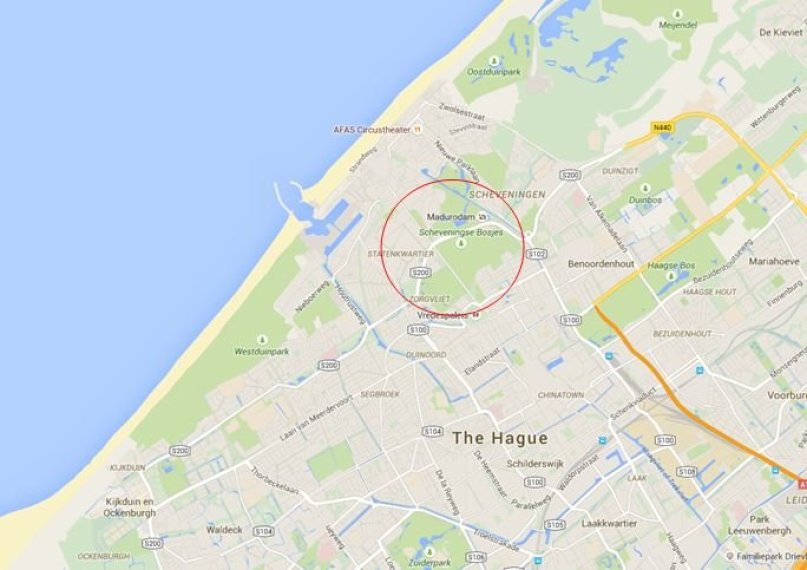關於納米比亞故事--從想逃跑,到離不開
想了很久的 納米比亞 ,想了很久的志願者活動。這個夏天,不顧家人和朋友的反對,一個人頭也不回地奔向 非洲 大陸......不緊張是假的,不激動也是假的。
快降落時望向窗外,“哇,這就是 非洲 大陸了嗎?”只透過小小的窗口也不難想象它的廣袤。 “我為什麼要來”前序航班延誤了,在約堡改簽的時候認識了幾個在 南非 工作的小伙。他們問我:“你去哪個國家?” “ 納米比亞 。” “一個人?第一次來 非洲 嗎?” “嗯。” “哇,我們都想盡辦法不去 納米比亞 ,你倒好,自己送上門。” 他的話嚇我一跳,“什麼...意思...” “ 納米比亞 可不是一個發達的國家,你一個人要註意安全,沒事就別在外面瞎逛了。如果真的遇到緊急情況,活著最重要,別管面子。”我一邊連連點頭,一邊半信半疑,“真的這麼恐怖嗎?”
“我為什麼要來”前序航班延誤了,在約堡改簽的時候認識了幾個在 南非 工作的小伙。他們問我:“你去哪個國家?” “ 納米比亞 。” “一個人?第一次來 非洲 嗎?” “嗯。” “哇,我們都想盡辦法不去 納米比亞 ,你倒好,自己送上門。” 他的話嚇我一跳,“什麼...意思...” “ 納米比亞 可不是一個發達的國家,你一個人要註意安全,沒事就別在外面瞎逛了。如果真的遇到緊急情況,活著最重要,別管面子。”我一邊連連點頭,一邊半信半疑,“真的這麼恐怖嗎?”
剛下飛機,熟悉的氣息撲面而來,這不是......我大AZ嗎。乾燥的風裡夾著熱烈的陽光,鋪天蓋地。
不過這下飛機沒有廊橋沒有擺渡,全靠步行,不免有點凄涼。一度地懷疑:我好歹也是到了一個國家的首都? 機場非常小,幾乎沒有接機大廳這個設施。取了行李沒走兩步就到大門了,不過這也很好找負責接機的人。
機場非常小,幾乎沒有接機大廳這個設施。取了行李沒走兩步就到大門了,不過這也很好找負責接機的人。
路上還看到驚喜地看到了華為大樓 酒店...不能叫酒店吧,像旅社,一層平房,用鑰匙開門的那種。房間小點我倒是無所謂,湊合一晚而已。但是浴室和廁所居然是公共的,這真的讓我一下子難以接受。在房間獃坐了好久才緩過神出去走走,其實是肚子餓了,想找點吃的。
酒店...不能叫酒店吧,像旅社,一層平房,用鑰匙開門的那種。房間小點我倒是無所謂,湊合一晚而已。但是浴室和廁所居然是公共的,這真的讓我一下子難以接受。在房間獃坐了好久才緩過神出去走走,其實是肚子餓了,想找點吃的。  來到吧台點了 三明 治和水,結果告訴我不能刷卡。這可難壞了在 香港 機場沒換到 納米比亞 幣,身上只有美金的我,有錢花不出去。有個熱心的小哥告訴我有家銀行可以換錢,還拿著地圖跟我比劃怎麼走。當時太陽已經快落山了,心裡牢記轉機時小伙的告誡,不要隨便單獨出門。謝過小哥後,就去廚房燒水喝。( 納米比亞 的自來水是可直接飲用的,但當時我能找到其他飲用水就不會願意喝。其實也是矯情,沒過幾天什麼都敢喝了。)
來到吧台點了 三明 治和水,結果告訴我不能刷卡。這可難壞了在 香港 機場沒換到 納米比亞 幣,身上只有美金的我,有錢花不出去。有個熱心的小哥告訴我有家銀行可以換錢,還拿著地圖跟我比劃怎麼走。當時太陽已經快落山了,心裡牢記轉機時小伙的告誡,不要隨便單獨出門。謝過小哥後,就去廚房燒水喝。( 納米比亞 的自來水是可直接飲用的,但當時我能找到其他飲用水就不會願意喝。其實也是矯情,沒過幾天什麼都敢喝了。)
小哥跟了上來,繼續解釋,“這裡的食材都可以用,你可以自己做飯。” 我看著七零八落,五顏六色的餐具和一大包一大包塞在透明冰箱里的麵包,尷尬地笑著謝謝他的提醒,畢竟對於我這個不通廚藝的人,用最快的方式把這壺水晾涼,可比做飯簡單多了。 天色還有點溫度,網絡卻慢到可憐,無所事事的我,在泳池邊坐著吹著風等著水涼,想回國的念頭愈發地強烈,實在沒忍住跟朋友們哭訴了一通才稍微得到緩解。仔細想想,這可是自己要死要活都要來的地方,總不能白來一趟吧。一邊安慰自己一邊往房間走去,進屋翻開臨走前奶奶硬塞在我包里的巧克力啃了起來,啃著啃著,剛剛平復的情緒又一下子被勾起。為了讓自己安穩地過完這晚,簡單的洗漱後,便鑽進被裡強迫自己開始倒時差。
天色還有點溫度,網絡卻慢到可憐,無所事事的我,在泳池邊坐著吹著風等著水涼,想回國的念頭愈發地強烈,實在沒忍住跟朋友們哭訴了一通才稍微得到緩解。仔細想想,這可是自己要死要活都要來的地方,總不能白來一趟吧。一邊安慰自己一邊往房間走去,進屋翻開臨走前奶奶硬塞在我包里的巧克力啃了起來,啃著啃著,剛剛平復的情緒又一下子被勾起。為了讓自己安穩地過完這晚,簡單的洗漱後,便鑽進被裡強迫自己開始倒時差。
睡醒第一次睜眼已然有點睡不著的感覺了,摸著黑點了下手機屏幕,夜裡兩點,絕望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連一覺睡到天亮這一點點事都變得奢侈。推開房門感受了一下屋外的氣氛,像起霜時的 武漢 ,但沒有那麼多水氣,冷得連樹葉閃過都沒有動靜。 “好像還可以?”在屋裡屋外來來回回走著折騰了一會後,終於安靜地躺回了床上。再一睜眼,看得見天色了,像完成了任務一樣開心。裹上一件外套和滿臉的蚊子包就出門洗漱準備吃飯。大家伙都起得很早,不小的廚房裡已經站滿了人。早餐非常簡陋,以至於我都不知道該從何拿起,最終只挑了個蘋果和一杯冰牛奶。 吃完早餐,收拾收拾東西,就在大堂等車來接我,去這次的目的地--Harnas。我申請了在Harnas兩周的動物保護志願者活動。暑假時間很緊,使勁擠才空出兩周,本來還嫌待得時間太短了,但是根據我昨晚的表現,估計兩周是明智的。
吃完早餐,收拾收拾東西,就在大堂等車來接我,去這次的目的地--Harnas。我申請了在Harnas兩周的動物保護志願者活動。暑假時間很緊,使勁擠才空出兩周,本來還嫌待得時間太短了,但是根據我昨晚的表現,估計兩周是明智的。
昨天前臺已經給我打過預防針了,“這裡的人都不怎麼守時,車應該不會按時到,等一兩個小時算是好的,我見過有人等了一天的......” 果不其然,等了將近三個小時,終於等來了接我的中巴。同行的還有兩個女生,一個 德國 人Alina,和一個 法國 人Marine。
坐上車後,就真正開始“深入敵後”了。可能是興奮和好奇,起那麼早還連著四個小時的顛簸,我愣是一點困意也沒有,目不暇接地看著窗外的景色:白屁股的狒狒抱著崽蹲在路邊左右不停地看著來往的車輛;三隻瘦瘦小小的疣豬排成一排從公路那頭穿到這頭,估計也是常客了,自信悠閑地知道我們一定會為他們讓路;路邊圍著牧場的柵欄可是攔不住這隻白牛的,他聰明得很,用角試探著撬動柵欄,最後 成功 伸出了前腿和半個身子;不知是什麼鳥將巢築成水滴狀懸在樹枝下,遠遠地看還以為是一顆顆果子......
看著這些入了迷,都是來不及舉起相機記錄的。戴上耳機,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心裡記下的,便是一個人的狂歡了。 快到達目的地之前有一段沙土路,顛得厲害。藏在車裡各個角落的沙子全都飛舞起來,我整個人被沙子大軍包圍,頭髮絲,指甲縫裡無處不有。嘴邊也全是細沙,抿下嘴,都是純正的大自然風味。等到達基地時,一行三人真真正正是“灰頭土臉”。
快到達目的地之前有一段沙土路,顛得厲害。藏在車裡各個角落的沙子全都飛舞起來,我整個人被沙子大軍包圍,頭髮絲,指甲縫裡無處不有。嘴邊也全是細沙,抿下嘴,都是純正的大自然風味。等到達基地時,一行三人真真正正是“灰頭土臉”。
很快,第一個挑戰就來了。我得拖著60多斤的箱子,走上一大段沙子路去往住宿的木屋。我這時整個人和箱子一起長在了土裡,只有四個字形容--紋絲不動。費盡了吃奶的力氣,才能將箱子慢慢往前挪,當然,早已被人高馬大的 歐洲 人甩在身後。等到了木屋後,已經沒力氣對住宿條件進行評判了,只知道費了這麼大力氣才住上的,怎麼都是好的。 這時正值西曬,陽光烤人,水被落在了剛剛的車上,急需水的時候卻被告知每天只有固定時刻固定地點才能買水。無奈乖乖找了個杯子接起水龍頭的水大口喝起來。其實還好,沒什麼特殊的味道,還算清冽。
這時正值西曬,陽光烤人,水被落在了剛剛的車上,急需水的時候卻被告知每天只有固定時刻固定地點才能買水。無奈乖乖找了個杯子接起水龍頭的水大口喝起來。其實還好,沒什麼特殊的味道,還算清冽。
晚上歡迎儀式結束後,天已經漆黑了,氣溫驟降得飛快,只得翻出羽絨服取暖。剛到基地還是一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姿態,哪怕被舍友告知了沒有熱水,也要硬著頭皮去洗個乾凈才肯睡覺,然後哆哆嗦嗦鑽進被窩。 宅家不好嗎?是沙發不夠軟,還是冰棒不夠甜開始前兩天工作還沒進入正軌,只是跟著熟悉各個動物。早上進行了am tour,人生第一次拿起生的驢肉喂動物們,只是被簡單地大卸八塊,沒有任何處理的,連著毛,帶著血的驢肉。掀開裝滿了驢肉的拖車,血淋淋的腥味撲鼻而來。輪到我喂 獅子 的時候,我站在旁邊不知從何下手,錶面上風平浪靜,氣定神閑,內心掙扎了千萬遍。
coordinator指揮著我找一塊驢頭,讓我揪著它的耳朵,方便拖出來。接觸到耳朵的瞬間,我便能感受到每一根粗礪的毛髮扎著我的手,冰冰涼,唯一一點溫熱,大概是還滴著的新鮮的血液。我真的低估了半個驢頭的重量,具體多重我也沒有概念,十幾斤?二十幾斤?反正是我一個一米六齣頭,不怎麼鍛煉的人難以舉起的分量,更別說要拋過高高的圍欄了。(之後又扔過幾次,無一例外的沒有 成功 ,每次我拋肉的時候,coordinator已經習慣性地站在旁邊等著撿起被我重重撞在圍欄上的肉,然後見怪不怪地上前一拋,再抓起一把沙子搓搓血漬,揚長而去。) 這是我第一次滿手沾滿了除我自己以外的動物的血,令人作嘔的苦腥讓我一下子難以接受,指甲縫裡,甚至指紋縫中都是慢慢變乾的、腥臭的血漬。無論怎麼用沙子“洗”都沒有辦法乾凈,反而沙子讓手變得乾燥粗糙。我開始反感,開始不耐煩,只想快點結束。 然而當你覺得自己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情後,這就結束了?Harnas永遠比你想象得狂野。
這是我第一次滿手沾滿了除我自己以外的動物的血,令人作嘔的苦腥讓我一下子難以接受,指甲縫裡,甚至指紋縫中都是慢慢變乾的、腥臭的血漬。無論怎麼用沙子“洗”都沒有辦法乾凈,反而沙子讓手變得乾燥粗糙。我開始反感,開始不耐煩,只想快點結束。 然而當你覺得自己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情後,這就結束了?Harnas永遠比你想象得狂野。
驅車前往下一個喂食點,遠遠地就看見鬣狗從四處竄跑出來,緊緊跟著我們的車。接下來,coordinator從車裡拿出一樣哪怕是隔著這麼長時間,我至今坐在電腦前都難以平復心情的東西--驢的大腸小腸。“Oh! No! Please...”面對如此“原生態”的大腸,徒手抓真是噩夢。剛開始我真的下不去手,只願意用三根手指把它揪起來,後來發現大腸極其重而且極其長,互相糾纏在桶里,根本不可能一根根扯出來,只能屏住呼吸然後一把抓丟下去。
鬣狗們相互威脅,撕扯,貪婪地叫著,享用他們的“美食”,而我在外面一個勁地反胃,眼淚在打轉。“為什麼我不在家好好獃著,要來找罪受。我今天把我一輩子都不會碰的東西都碰了個遍。”
 一波三折,在接下來喂獰貓的時候,我跟著coordinator進入圍欄裡面,結果光榮負傷......回到房間,舍友Sabrina問我:“今天的AM Tour怎麼樣?”我苦澀地笑道:“我得到了一個驚喜。” “怎麼了?” 我伸出還攥著一盒剛剛 中國 朋友給的創口貼的手,“今天喂獰貓的時候,我進圍欄了。” “Oh my god,你進去了!” “嗯,有隻獰貓躲在深處的樹林里,我們只能進去喂它。我拿著肉,沒有察覺另一隻獰貓已經繞到了我的身後。當我準備擲出肉的一瞬間,它猛地撲上來從我手中搶走了肉......” 我至今還記得它那寬厚堅硬又冰冷的爪子是如何嵌進我的肉里,以我從來沒有領教過的速度。
一波三折,在接下來喂獰貓的時候,我跟著coordinator進入圍欄裡面,結果光榮負傷......回到房間,舍友Sabrina問我:“今天的AM Tour怎麼樣?”我苦澀地笑道:“我得到了一個驚喜。” “怎麼了?” 我伸出還攥著一盒剛剛 中國 朋友給的創口貼的手,“今天喂獰貓的時候,我進圍欄了。” “Oh my god,你進去了!” “嗯,有隻獰貓躲在深處的樹林里,我們只能進去喂它。我拿著肉,沒有察覺另一隻獰貓已經繞到了我的身後。當我準備擲出肉的一瞬間,它猛地撲上來從我手中搶走了肉......” 我至今還記得它那寬厚堅硬又冰冷的爪子是如何嵌進我的肉里,以我從來沒有領教過的速度。
我可不是報喜不報憂的人(笑),一點委屈都得跟家人分享。乾媽最有意思,知道我受傷了,操著口海派普通話,著急忙慌:“哎呦丫頭哇,實在不行就逃回來吶,我帶你到其他地方做志願者吶,這個地方嚇死人得。” 我跟她打趣道:“我來這花了很多錢噠,你給我報機票我就回去。” “好的哇好的哇,乾媽很 大方 的哦,你快點回來吶,我給你報機票......” 乾媽的話讓我哭笑不得,不過想想,現在逃回去,也太不值了,經歷雖然苦,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機會扛驢頭、扯大腸、被獰貓撓的。就暫且這麼安慰自己吧。 只要不圍攻我,我可以考慮跟你們和睦相處經歷了am tour的“摧殘”後,bamboo walk是我覺得目前為止最棒的活動,前提是他們願意收斂起利爪和後槽牙。bamboo walk之前,我與狒狒進行了初次接觸,一進柵欄里,他們就像外敵入侵一樣瘋狂地嘶叫。我顫顫巍巍地在他們中間坐下,突然其中一隻就開始湊在我身上翻我的口袋,翻得那叫一個細緻。可能是沒有找到想要的東西,或者只是想跟我玩,突然抱著我的右腿就咬了上來,完全不等我反應,就已經感受到他後槽牙的力量了。我沒忍住尖叫了一聲,又迅速地反應過來捂住了嘴。可是還是來不及了,另一隻狒狒突然從上面跳下來扯著我的胳膊又是一口。一瞬間,我被狒狒們群起圍攻了(攤手),在coordinator的幫助下我才免遭“毒手”。我心想,完了,又是一種我惹不起的動物。
與遛狗不一樣,狒狒更像是小孩,他們會互相站立打鬧,會邊走邊摸索地上的鹽巴,累了還會耍賴撒嬌要抱抱。當然,他們咬人和在你肩膀上吃喝拉撒的功力可是難以小覷,不把你渾身弄得兮臟他們是不會罷休的。 水池是狒狒們的根據地,也是我們的休息站。連跑帶叫地瘋了一路,我早就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找個陰涼地方坐著。狒狒們可是撒開了玩,沒有人比他們更熟悉這裡的地形。他們知道哪個食槽裡面有殘留的食物,知道哪根樹枝能盪得最遠,知道大羚羊和野馬都是善意,無需顧慮。
第一次bamboo walk時沒有經驗,口渴了之後就蹲下去喝水管的水。結果狒狒們呼啦一下子衝上來濺起一片水花,再從我背上越過,玩的好不自在。留下一個渾身濕漉漉,頭髮沾滿了泥的我茫然地站在那。“所以我剛剛是被當作鞍馬了嗎?” “他們只是好奇你在乾什麼。”“我瞭解,但這也太偏激了。”我和Marine哭笑不得地相視一笑。 大羚羊和跳羚悠閑地在水池邊晃悠,被吵鬧的狒狒吸引了去,竟和我們一樣,盯著他們不放。當然,羚羊們也可能是被我們吸引了去,就像他們也在吸引著我。被狒狒們“欺負”之餘,其實也沒有那麼糟糕。
大羚羊和跳羚悠閑地在水池邊晃悠,被吵鬧的狒狒吸引了去,竟和我們一樣,盯著他們不放。當然,羚羊們也可能是被我們吸引了去,就像他們也在吸引著我。被狒狒們“欺負”之餘,其實也沒有那麼糟糕。 
 (有些人錶面光鮮靚麗,背地裡已經被尿了一身......)
(有些人錶面光鮮靚麗,背地裡已經被尿了一身......)  逐漸適應瘋狂得空的時候,我喜歡自己在農場獃著,跟豬啊鴨啊羊啊窩在一起,也不做什麼,也不想什麼,就是發獃,能待好久。如果信號好的話還能跟爺爺奶奶視頻。
逐漸適應瘋狂得空的時候,我喜歡自己在農場獃著,跟豬啊鴨啊羊啊窩在一起,也不做什麼,也不想什麼,就是發獃,能待好久。如果信號好的話還能跟爺爺奶奶視頻。
“你在那待著多好啊,你在上大學,在上一所世界上最好的大學。這所大學里不僅有世界各地不同的人,還有各種生靈,你在學著的是如何跟他們好好相處。在地球的另一端,你經歷著別人經歷不了的,也就看到別人難以理解的視野......”聽完,想了想,現在的日子好像也沒有那麼苦了。
 下午的cheetah walk好像放得開了,我不再那麼關心我的衣服是不是會臟,手是不是會破。我開始可以跟組員一起席地而坐甚至打滾。靈感來了,再比比誰模仿獵豹更像。由著獵豹們活動活動筋骨,我們就坐地上玩著又爛又蠢的文字游戲。雖然我總是輸,但又有誰會在意呢。
下午的cheetah walk好像放得開了,我不再那麼關心我的衣服是不是會臟,手是不是會破。我開始可以跟組員一起席地而坐甚至打滾。靈感來了,再比比誰模仿獵豹更像。由著獵豹們活動活動筋骨,我們就坐地上玩著又爛又蠢的文字游戲。雖然我總是輸,但又有誰會在意呢。  在Harnas,工作一直都是辛苦的(時隔半年,我依舊這麼覺得),但是讓你愛上它的是這裡的人和動物們的善良和自由。
在Harnas,工作一直都是辛苦的(時隔半年,我依舊這麼覺得),但是讓你愛上它的是這裡的人和動物們的善良和自由。 

 開始瞭解你,從Amarula中繁星初上,晚餐中心的篝火成了氣溫驟降的寒冬里唯一的火光。大家圍坐在側,每周離去的人將他自己的故事講進Amarula里,再把它留下來。我才發現,這幫十幾二十多歲與我同齡的人有著比我想象的更強大的內心和力量。
開始瞭解你,從Amarula中繁星初上,晚餐中心的篝火成了氣溫驟降的寒冬里唯一的火光。大家圍坐在側,每周離去的人將他自己的故事講進Amarula里,再把它留下來。我才發現,這幫十幾二十多歲與我同齡的人有著比我想象的更強大的內心和力量。 
 他們有的人利用gap year來這兒與熱愛的動物們生活在一起;有的人辭掉了 巴黎 高薪的工作來體驗另一極端的生活;有人即將前往 英國 深造並堅定了為動物保護事業奉獻一生的決心,把Harnas作為自己頗具儀式感的起點;還有的人似乎把自己弄丟了,來這孤世里找回自己......他們把城市裡的光鮮放在背後,盤塊頭巾,扯件T恤,以臉上的曬斑為美,以身上的傷痕為紀念。看著自己胳膊上即將消失的疤痕,我開始不停回想那一天天被meerkat咬,被狒狒撓的日子,我終究還是沒有那麼討厭他們對我的攻擊。
他們有的人利用gap year來這兒與熱愛的動物們生活在一起;有的人辭掉了 巴黎 高薪的工作來體驗另一極端的生活;有人即將前往 英國 深造並堅定了為動物保護事業奉獻一生的決心,把Harnas作為自己頗具儀式感的起點;還有的人似乎把自己弄丟了,來這孤世里找回自己......他們把城市裡的光鮮放在背後,盤塊頭巾,扯件T恤,以臉上的曬斑為美,以身上的傷痕為紀念。看著自己胳膊上即將消失的疤痕,我開始不停回想那一天天被meerkat咬,被狒狒撓的日子,我終究還是沒有那麼討厭他們對我的攻擊。 
 向宿舍走去,氣溫驟降的夜晚,給人慰藉的除了羽絨服還有如約而至的星空。可能過於冷了,氣息慢慢變緩,慢慢變得不能察覺,此時星空仿佛也跟著呼吸變得靜止,往下沉,再往下沉,離我越來越近。我不想伸手去夠,怕真的攪動了銀河,也怕冷。
向宿舍走去,氣溫驟降的夜晚,給人慰藉的除了羽絨服還有如約而至的星空。可能過於冷了,氣息慢慢變緩,慢慢變得不能察覺,此時星空仿佛也跟著呼吸變得靜止,往下沉,再往下沉,離我越來越近。我不想伸手去夠,怕真的攪動了銀河,也怕冷。  “瘋狂”的德國人在志願者的隊伍里還有兩位年紀稍大的 德國 人:Angelica和她的丈夫。在異國他鄉,他們可就真成了我自己的爺爺奶奶。一天早上剛到工作崗位,露水都還沒散去,我被凍得不輕,臉和鼻子都通紅。Angelica見到我,一路小跑過來托著我的臉問我是不是感冒了,讓我多穿點。我倒是沒反應過來,愣了好久,才答道:“是有點冷,但我身體挺好的。” 還有一次我在準備動物們的早餐,不知道什麼時候Angelica走到了我身邊,接過我手裡的桶放在了地上,然後貼心地幫我把袖子一折一折地輓上去。“Angelica,你太sweet,我以後會離不開你的。”我一邊跟她打趣,一邊在心裡感動好久。誰料爺爺在旁邊悠悠地補了一刀:“她也許不是為了你,只是覺得你這樣幹活快一點。”
“瘋狂”的德國人在志願者的隊伍里還有兩位年紀稍大的 德國 人:Angelica和她的丈夫。在異國他鄉,他們可就真成了我自己的爺爺奶奶。一天早上剛到工作崗位,露水都還沒散去,我被凍得不輕,臉和鼻子都通紅。Angelica見到我,一路小跑過來托著我的臉問我是不是感冒了,讓我多穿點。我倒是沒反應過來,愣了好久,才答道:“是有點冷,但我身體挺好的。” 還有一次我在準備動物們的早餐,不知道什麼時候Angelica走到了我身邊,接過我手裡的桶放在了地上,然後貼心地幫我把袖子一折一折地輓上去。“Angelica,你太sweet,我以後會離不開你的。”我一邊跟她打趣,一邊在心裡感動好久。誰料爺爺在旁邊悠悠地補了一刀:“她也許不是為了你,只是覺得你這樣幹活快一點。”  爺爺奶奶沒有孩子,這倒也讓二老格外清閑,世界各地走走逛逛噹噹志願者,施展一下依舊健朗的腰身。每天跟著我們一起開會、準備食物、喂養動物、打掃衛生,真羡慕他們的身子骨和精氣神。
爺爺奶奶沒有孩子,這倒也讓二老格外清閑,世界各地走走逛逛噹噹志願者,施展一下依舊健朗的腰身。每天跟著我們一起開會、準備食物、喂養動物、打掃衛生,真羡慕他們的身子骨和精氣神。
我們照常在操作臺上切著生肉,幾位 德國 女生在旁邊手舞足蹈她們新編的歌曲。Angelica翹了翹下巴說:“看!瘋狂的 德國 人們”,我笑著對她說:“不,你才是‘瘋狂’的 德國 人。”
 記憶,在日落獅吼中被加深每天最愛的時光就是和大伙待在夕陽下,走路或坐敞篷車都行,去哪都行。音響里放著Walking with the san,周圍圍繞著大家一天所有的話題,享受著太陽落下前一個小時不冷不熱的舒坦。然後一起坐在高處,守著太陽一點一點落下......
記憶,在日落獅吼中被加深每天最愛的時光就是和大伙待在夕陽下,走路或坐敞篷車都行,去哪都行。音響里放著Walking with the san,周圍圍繞著大家一天所有的話題,享受著太陽落下前一個小時不冷不熱的舒坦。然後一起坐在高處,守著太陽一點一點落下......
快降落時望向窗外,“哇,這就是 非洲 大陸了嗎?”只透過小小的窗口也不難想象它的廣袤。

剛下飛機,熟悉的氣息撲面而來,這不是......我大AZ嗎。乾燥的風裡夾著熱烈的陽光,鋪天蓋地。
不過這下飛機沒有廊橋沒有擺渡,全靠步行,不免有點凄涼。一度地懷疑:我好歹也是到了一個國家的首都?

路上還看到驚喜地看到了華為大樓


小哥跟了上來,繼續解釋,“這裡的食材都可以用,你可以自己做飯。” 我看著七零八落,五顏六色的餐具和一大包一大包塞在透明冰箱里的麵包,尷尬地笑著謝謝他的提醒,畢竟對於我這個不通廚藝的人,用最快的方式把這壺水晾涼,可比做飯簡單多了。

睡醒第一次睜眼已然有點睡不著的感覺了,摸著黑點了下手機屏幕,夜裡兩點,絕望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連一覺睡到天亮這一點點事都變得奢侈。推開房門感受了一下屋外的氣氛,像起霜時的 武漢 ,但沒有那麼多水氣,冷得連樹葉閃過都沒有動靜。 “好像還可以?”在屋裡屋外來來回回走著折騰了一會後,終於安靜地躺回了床上。再一睜眼,看得見天色了,像完成了任務一樣開心。裹上一件外套和滿臉的蚊子包就出門洗漱準備吃飯。大家伙都起得很早,不小的廚房裡已經站滿了人。早餐非常簡陋,以至於我都不知道該從何拿起,最終只挑了個蘋果和一杯冰牛奶。

昨天前臺已經給我打過預防針了,“這裡的人都不怎麼守時,車應該不會按時到,等一兩個小時算是好的,我見過有人等了一天的......” 果不其然,等了將近三個小時,終於等來了接我的中巴。同行的還有兩個女生,一個 德國 人Alina,和一個 法國 人Marine。
坐上車後,就真正開始“深入敵後”了。可能是興奮和好奇,起那麼早還連著四個小時的顛簸,我愣是一點困意也沒有,目不暇接地看著窗外的景色:白屁股的狒狒抱著崽蹲在路邊左右不停地看著來往的車輛;三隻瘦瘦小小的疣豬排成一排從公路那頭穿到這頭,估計也是常客了,自信悠閑地知道我們一定會為他們讓路;路邊圍著牧場的柵欄可是攔不住這隻白牛的,他聰明得很,用角試探著撬動柵欄,最後 成功 伸出了前腿和半個身子;不知是什麼鳥將巢築成水滴狀懸在樹枝下,遠遠地看還以為是一顆顆果子......
看著這些入了迷,都是來不及舉起相機記錄的。戴上耳機,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心裡記下的,便是一個人的狂歡了。

很快,第一個挑戰就來了。我得拖著60多斤的箱子,走上一大段沙子路去往住宿的木屋。我這時整個人和箱子一起長在了土裡,只有四個字形容--紋絲不動。費盡了吃奶的力氣,才能將箱子慢慢往前挪,當然,早已被人高馬大的 歐洲 人甩在身後。等到了木屋後,已經沒力氣對住宿條件進行評判了,只知道費了這麼大力氣才住上的,怎麼都是好的。

晚上歡迎儀式結束後,天已經漆黑了,氣溫驟降得飛快,只得翻出羽絨服取暖。剛到基地還是一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姿態,哪怕被舍友告知了沒有熱水,也要硬著頭皮去洗個乾凈才肯睡覺,然後哆哆嗦嗦鑽進被窩。 宅家不好嗎?是沙發不夠軟,還是冰棒不夠甜開始前兩天工作還沒進入正軌,只是跟著熟悉各個動物。早上進行了am tour,人生第一次拿起生的驢肉喂動物們,只是被簡單地大卸八塊,沒有任何處理的,連著毛,帶著血的驢肉。掀開裝滿了驢肉的拖車,血淋淋的腥味撲鼻而來。輪到我喂 獅子 的時候,我站在旁邊不知從何下手,錶面上風平浪靜,氣定神閑,內心掙扎了千萬遍。
coordinator指揮著我找一塊驢頭,讓我揪著它的耳朵,方便拖出來。接觸到耳朵的瞬間,我便能感受到每一根粗礪的毛髮扎著我的手,冰冰涼,唯一一點溫熱,大概是還滴著的新鮮的血液。我真的低估了半個驢頭的重量,具體多重我也沒有概念,十幾斤?二十幾斤?反正是我一個一米六齣頭,不怎麼鍛煉的人難以舉起的分量,更別說要拋過高高的圍欄了。(之後又扔過幾次,無一例外的沒有 成功 ,每次我拋肉的時候,coordinator已經習慣性地站在旁邊等著撿起被我重重撞在圍欄上的肉,然後見怪不怪地上前一拋,再抓起一把沙子搓搓血漬,揚長而去。)
驅車前往下一個喂食點,遠遠地就看見鬣狗從四處竄跑出來,緊緊跟著我們的車。接下來,coordinator從車裡拿出一樣哪怕是隔著這麼長時間,我至今坐在電腦前都難以平復心情的東西--驢的大腸小腸。“Oh! No! Please...”面對如此“原生態”的大腸,徒手抓真是噩夢。剛開始我真的下不去手,只願意用三根手指把它揪起來,後來發現大腸極其重而且極其長,互相糾纏在桶里,根本不可能一根根扯出來,只能屏住呼吸然後一把抓丟下去。
鬣狗們相互威脅,撕扯,貪婪地叫著,享用他們的“美食”,而我在外面一個勁地反胃,眼淚在打轉。“為什麼我不在家好好獃著,要來找罪受。我今天把我一輩子都不會碰的東西都碰了個遍。”
我可不是報喜不報憂的人(笑),一點委屈都得跟家人分享。乾媽最有意思,知道我受傷了,操著口海派普通話,著急忙慌:“哎呦丫頭哇,實在不行就逃回來吶,我帶你到其他地方做志願者吶,這個地方嚇死人得。” 我跟她打趣道:“我來這花了很多錢噠,你給我報機票我就回去。” “好的哇好的哇,乾媽很 大方 的哦,你快點回來吶,我給你報機票......” 乾媽的話讓我哭笑不得,不過想想,現在逃回去,也太不值了,經歷雖然苦,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機會扛驢頭、扯大腸、被獰貓撓的。就暫且這麼安慰自己吧。 只要不圍攻我,我可以考慮跟你們和睦相處經歷了am tour的“摧殘”後,bamboo walk是我覺得目前為止最棒的活動,前提是他們願意收斂起利爪和後槽牙。bamboo walk之前,我與狒狒進行了初次接觸,一進柵欄里,他們就像外敵入侵一樣瘋狂地嘶叫。我顫顫巍巍地在他們中間坐下,突然其中一隻就開始湊在我身上翻我的口袋,翻得那叫一個細緻。可能是沒有找到想要的東西,或者只是想跟我玩,突然抱著我的右腿就咬了上來,完全不等我反應,就已經感受到他後槽牙的力量了。我沒忍住尖叫了一聲,又迅速地反應過來捂住了嘴。可是還是來不及了,另一隻狒狒突然從上面跳下來扯著我的胳膊又是一口。一瞬間,我被狒狒們群起圍攻了(攤手),在coordinator的幫助下我才免遭“毒手”。我心想,完了,又是一種我惹不起的動物。
與遛狗不一樣,狒狒更像是小孩,他們會互相站立打鬧,會邊走邊摸索地上的鹽巴,累了還會耍賴撒嬌要抱抱。當然,他們咬人和在你肩膀上吃喝拉撒的功力可是難以小覷,不把你渾身弄得兮臟他們是不會罷休的。 水池是狒狒們的根據地,也是我們的休息站。連跑帶叫地瘋了一路,我早就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找個陰涼地方坐著。狒狒們可是撒開了玩,沒有人比他們更熟悉這裡的地形。他們知道哪個食槽裡面有殘留的食物,知道哪根樹枝能盪得最遠,知道大羚羊和野馬都是善意,無需顧慮。
第一次bamboo walk時沒有經驗,口渴了之後就蹲下去喝水管的水。結果狒狒們呼啦一下子衝上來濺起一片水花,再從我背上越過,玩的好不自在。留下一個渾身濕漉漉,頭髮沾滿了泥的我茫然地站在那。“所以我剛剛是被當作鞍馬了嗎?” “他們只是好奇你在乾什麼。”“我瞭解,但這也太偏激了。”我和Marine哭笑不得地相視一笑。


“你在那待著多好啊,你在上大學,在上一所世界上最好的大學。這所大學里不僅有世界各地不同的人,還有各種生靈,你在學著的是如何跟他們好好相處。在地球的另一端,你經歷著別人經歷不了的,也就看到別人難以理解的視野......”聽完,想了想,現在的日子好像也沒有那麼苦了。







我們照常在操作臺上切著生肉,幾位 德國 女生在旁邊手舞足蹈她們新編的歌曲。Angelica翹了翹下巴說:“看!瘋狂的 德國 人們”,我笑著對她說:“不,你才是‘瘋狂’的 德國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