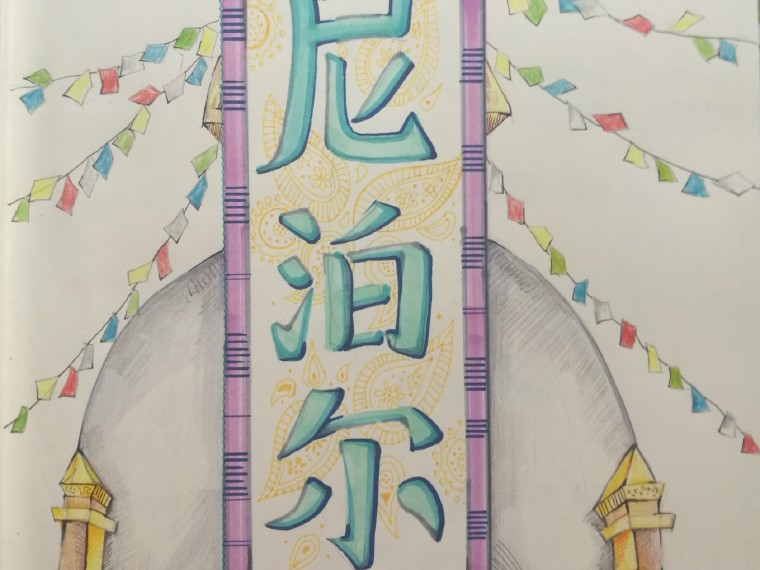22加德滿都,睜不開兩眼看命運光臨(泰米爾)
早餐開飯的越來越晚,雖然知道要坐很顛的車,來時的經驗告訴我我必須多吃。兩盤草莓醬和黃油抹麵包下肚,我一個人狂野的把箱子搬來搬去。大粉象在石子路上再次發出了不滿,引得工作人員一個招手,喚來了員工給我提。我剛說完謝謝,他就拉著箱子一路暴走。這不就是換了個方式折磨它嘛。“請別這樣。”員工這才盡職的提著它放到了車上。這輛車上還多了其他的 中國 人,那一家三男三女的兄弟姐妹,還有同樣自己走的各位。我們都在車旁等著,因為正在倒著走的車輛正好卡在了電線上。一位小哥見怪不怪,爬上汽車一邊理線一邊指揮司機。這回他沒有拍車體告訴司機還有多少倒車距離,直接拍車頂,拍聲越急就是越快碰到牆了。經歷過兩次長途的我,為了避免顛簸坐到了前面,卻被小哥轟到最後面的最角落。我不甘心的瞥了他一眼,還賜了個Why,但還是乖乖的挪走。我知道他有他的原因,但這種原因他們從不解釋。看在他拗不過我的倔脾氣對我一路抱著尼康的大包不放上行李架表示OK,我也就沒有說話。路上的風塵依舊很大。不過這輛車是有空調並且開空調的,門窗自然就緊了點。路上不斷上來的當地人把座位一個個填滿。我前面的狐臭少女執拗的想讓我開窗,我看她粗黑打綹的長髮不想多解釋,開了之後把我身側的窗戶又用窗帘擋住,她也欲言又止。除了暈車的不幸人士(他們多數已經鼓起了嘴正存著貨),大家都累極了。我右邊的大媽,即使帶了好幾個大鑽戒和金色手錶,也不顧形象的呼呼大睡。空調早已關閉,呼吸的熱氣漸漸把車廂的氣氛弄得污濁。停車吃飯的十五分鐘,是我們短暫的驚蟄。我依舊什麼都不買,使勁塞自己糖。畢竟最後一排是整輛車裡最悶熱最顛簸的地方,不暈車的我也感覺有點彆扭了。在路邊小攤涼蔭下等著車門打開的我,和狐臭女有了短暫的交流。我能看出她是富家孩子,她和他父親的打扮算是當地人里前衛的,並且花了和我們外國游客一樣的500rs的票價。我們談本地大學、貨價和 印度 人,卻總有人托著盤子問我們需不需要黃瓜。惹得小姑娘開玩笑說,“我需要在這裡掛一個牌子,‘我什麼都不要'。”在買東西上,歐美人就十分 大方 。一根手指大的香蕉要價10rs根本無需砍價,話都不說給錢就走。我和當地人聊天總忘不了問物價,於是也悄悄地問這個女孩兒, 比如 香蕉多少錢一斤,她卻不食人間煙火,問什麼都不知道。在談話的結尾,她像所有人一樣說我友好,我說大家都友好,所以我才也同樣地回應。不知道是第幾次表達了對這個國家深刻的愛和對 印度 強烈的厭後,車門終於開了。她拿著她父親給她買的還沒 開封 的水問我需不需要,我則友好的拒絕,反而遞了塊糖,她當然也不好意思沒有收下。後來到了泰米爾附近時,兩位和我打了招呼,沒多說就下車了。聽說回加都並不需要那麼久,但是這趟旅程直到四點才讓我們見到人煙。從八點到現在,已經走了八個小時了。我不想去戳我的腿腳看有沒有浮腫,因為肯定有了,我的鞋已經有點發緊,而它的主人我,渾身無力。到了加都的汽車像是腸胃不好的病人,車身貼著的雨就是它難受出的虛汗。它一路走走停停總要拉稀——誰需要在哪裡下車,它就在哪裡停。雖然這時溫度不高,車內卻因為不安分和勞累充斥著焦躁。現在剩下的就只有游客了,其中大部分都是 中國 人。我們一直在等著終點,等著這趟傳說只要六七個小時而我們走了八個小時四十分鐘的車停下。星星月亮都盼到了,車也就停了。但是說實話,那一刻我沒覺得特別累。反而是很暢快, 奇特旺 的旅程是我這一路上最壓抑的部分。剛到加都的時候是新鮮,到 博卡拉 的時候有同伴,而 奇特旺 這個可憐的孩子既沒有我給的新鮮感和興奮感,也沒有自己與眾不同的魅力,被我列為必須逃脫地點之一。我沒有多想,看到大粉象灰頭土臉的被卸下來後馬上找 四川 六兄妹想搭車一起去泰米爾——我不想再面對大媽了。可是這家其中的一個女生因為暈車正蹲坐在地上,讓他們不得不原地找旅館。那我就一個人。正擼袖子準備在積水的下坡扛行李的我一個抬頭,和在 博卡拉 最破的旅游車上遇到的給我糖的姐姐再次偶遇,她被一對情侶中的女生拒絕後,正和一堆外國背包客一起尋找泰米爾,被我召喚著脫離了隊伍,打算和我一起走到那裡。一路的上坡和下坡傾斜度很大,我開始因為水坑提著大粉象在走,後來有車橫衝直撞怕自己反應不過來就拉著,再後來有一個大上坡,我就像推貨車一樣靠濕滑地面的摩擦力,頂著行李箱上坡。剛進入泰米爾的路口,剛好就在Shree Tibet Family Guest House附近,我不想再見到那個“教育”我的老闆,想在Hotel Impala拿完我的志願證書後直接走掉。那個給我糖的 泉州 姐姐十分耐心地在外面幫我看東西,而我實在忍不住多瞥幾眼在Hotel Impala沙發上穿著紅衣T恤的負責人Bijay。他不但不回我的所有信息,還閑適地正和碧眼妹妹談著志願的事情。不知道為什麼,前臺並沒有直接回答我單間的價格,反而一個請的姿勢讓我問Bijay。我就想試試他是不是個讓我討厭的人,揚著眉毛看著他,沒想到他果然不負我,給了我一個虛高價格。我很想寫出來供大家參考,但是鬼才想記得他說過的屁話。 泉州 姐姐在我出來後十分配合地提供了流量,供我查詢圓夢旅館的位置。這時那個碧眼妹子猶猶豫豫地過來,向我詢問哪裡可以換匯。我也告訴她不要再街上換,不知道可不可以,還是推薦她去問問 中國 旅館和餐廳。她也恍然 大悟 ,乾脆地說完謝謝就走。想問我們事情的不止有她,還有許多拿著小冊子和名片的酒店員工。其中那個因為我不認路,主動給我他自己影印的地圖的大叔也在。絕對是他,他穿戴整齊身材高大,走路會稍微駝背低頭,襯衫掖在淺藍牛仔褲里。我的眼神已經出來,可在我打招呼之前他先開了口,“住酒店嗎,一晚上只要25美金。”我像是不相信男朋友變心的痴情女,帶著期待,“你知道嗎,我覺得我們之前見過的。我有次迷路,是你把我送回去的?”直到現在我才覺得這句話有點不對勁,好像我在等著被撩一樣。其實真的不是,我只是在尋找這個城市給我的記憶。這位大叔是教我愛上 尼泊爾 的第一人,自他起,我願意並且主動看到當地人的善良。因為他們心裡那顆做善事不多解釋,時刻blingbling的心,我即使一個人走,也很少懼怕危險。我每天起床的動力其實不是看寺廟,那些屹立在那裡十幾個世紀坍塌下來就一次地震的建築,總比不上當地人文的魅力大。我喜歡和當地人說“打擾了”,“謝謝”和“你人真好”,好像我也是善良的一樣。我友好時,世界都是友好的。我不再擔心政治、毒品、平等和糧食,我只關心我和我身邊的事物,正常一個正常人的正常。但是大叔只顧著推銷自己的旅館,“哦是嗎,也許吧,你看看這個。”不是我看錯了,真的是他。但是也真的不是他。我不想在說什麼,再多一句我的信任就會像雨後的螞蟻窩一樣,於是急匆匆地走掉。我們拒絕花150尼幣也就是人民幣八塊九毛八坐人力車,當地人操著聽不懂的咖喱味語言說了無數個impossible,我也說了無數個I will show you impossible。然後我就像個帶絕症孩子看病的母親一樣深憋了一口氣,一個過肩側背起了二十公斤的箱子。當然身上還帶著絕望母親標配——大包小包十公斤。有些司機依然跟在我後面,Come on, you can't, too long. This is not water, this, river.褲子小腿以下是濕的,路邊小哥手機里的我是笑的。我不管,我托,我拉,我舉,我提,我能。有些在路邊喝咖啡的外國人看到脖子上繫著毛巾,帶著冰袖的活脫脫的農民我,都不免皺眉頭。這種表情我再熟悉不過,一個不知道是嘲諷自己還是他們的笑自動溜出,他們也就笑了。在每個路口,我們都要猶豫向哪裡走。 泉州 姐姐杏仁手裡的谷歌地圖更新得十分有趣,距離和位置每走兩步都不一樣,站在原位每刷新一次都不同。搞得我們十分鐘的路程饒了二三十分鐘。地圖上的步行時間一直在跳躍,一會兒長一會兒短。杏仁不像我,遇到主動幫忙的 尼泊爾 人會友善的回應,她信人不如信己,總是背對著想幫忙的當地人說No,頭也不抬的看手機查地圖。所以當不穩定的谷歌地圖也尬尷著刷新時,我就四處問當地人應該怎麼走。在最後的一個路口,那家飯店的小哥建議我打車,我看著杏仁手裡幫我提著的牛仔包,從沒那麼自信地說,“那麼長我都走過來了。” 其實我們都不缺那錢,我們都只是想看看自己能把自己逼到什麼程度。我們終於在錯過與轉向中走到主路,以周圍建築物判斷圓夢旅館的位置。把行李推進圓夢的我,剛好看見師父極光,他見我的驚訝程度不亞於我見他的。好心的他幫我把行李拿上樓後還幫我和總是不高興臉的老闆娘砍價。不高興看著頭頂標記著每件客房的狀態的牌子,“住的貴一點可以嗎?”我想都沒想,“多兩盧比我都不願意。”除了不高興大家都笑了,杏仁十分配合地一路跟著我,沒多想圖方便就和我住一家旅館。所以最後我們住了間標間,兩人均攤下來比四人間的床位還便宜50rs。 
 剛進屋的我正被極光嘲笑著來的正是時候,他要請將要離開的帳篷吃飯。我囑咐杏仁別忘鎖門後,把行李放下,沒多想就直接走了。這時我才意識到自己渾身是泥,鞋裡都可以養泥鰍了。在門外的公用衛生間,當著師傅極光的面,我腿在空中畫了個半圓直接落到池子里,我要在穿著褲子襪子和鞋的情況下把自己洗乾凈——剛剛咱可是過了泰米爾這條河——極光沒說話,他獃住了。帳篷見到我有點吃驚,她沒想再碰到我。雖然我是她好不容易碰到的女孩子,我倆卻互相不喜歡。她把朋友當導游以自我為中心。我第一次去博大哈佛塔就是和她一起的,她圍著極光瞎問,整個人控制著我們隊伍的速度和方向,在夢想花園時也是。不想留篇幅給她,我們氣場不合。吃飯的那家 重慶 餐館就在圓夢出門右拐不遠,菜價和國內一樣,但是味道挺不錯。店內好像沒開抽油煙機,四壁也沒有窗戶,我只能不停地咳嗽流眼淚。雖然看出了帳篷因為我打攪她這頓二人餐很不爽,我也沒走——能少花錢就少花錢,走到今天我經歷了太多,我不要臉,我要吃免費的晚餐。我們等菜的時候,服務員小哥一個ok揚手就走,正好讓我看見了他右腋下的衣服洞。真是副風景啊,小叢林剛好從裡面冒出來。我指給極光看,“這哥們兒腋下漏了個洞。”小哥雖然覺得我沒說好話,也不好意思多問,直接走掉了。但是極光反應比較大,把正喝著的一口水吐在了帳篷衣服上。到現在我還享受著有潔癖的帳篷的表情,好像我教唆豬把她的乾凈白菜給拱了一樣。就沖她這表情,這頓飯就是吃屎我也高興。飯菜馬上端上,但是帳篷半截就被一個路上遇到的姑娘叫去幫忙帶東西回國。我儘量剋制著貪吃的心,慢慢但不停地夾菜。回來時,一桌的菜剩的不多了,我提議和極光一起請帳篷,再點點兒菜,帳篷自然是婉拒了。我以為極光會送帳篷回去,結果倆人就在旅館前揮了個手,馬上分道揚鑣。送完她轉身進旅館的極光還在跟我說,“你個丫頭,來了也不告訴我一聲,我去接你啊。”我先告別了極光,想在路邊買芒果。 尼泊爾 的水果又大又甜,雖然裡面有時候會有點小蟲,吃的時候要註意一下,我也依舊難割捨對水果的愛。坦白講,我可以好幾個禮拜只吃水果過活,我也不是沒這麼乾過。連舍友都說我的胃會被這些小妖精搞壞,我也不管,我就是喜歡花錢買它們。它們長得那麼可愛,肥嫩多汁滿面紅光。我最高興的事就是在上午花兩個小時吃水果,看著它們水靈靈的倒在我的盤中,我最享受咬完一口後它們默默流下的汁水,有時因為擠破果肉而發亮的身體,它們沉默的樣子好像被我欺負的小姑娘。天啊,太爽了。但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我討厭香蕉和榴蓮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它們不好吃,是因為它們不可愛,被我欺負後沒有吐露真情,像個憨憨的傻兒子。總之,我愛水果,水果愛我!我在右拐直走,遇到了我在 尼泊爾 第一次買水果時的小販,他那張姦商臉我真的忘不了。我告訴他我們見過,他卻糊弄著說是的是的我記得,手裡擺弄著芒果眼睛瞟向別處。想到他上次想騙我錢的架勢和這次的虛高價,我轉頭就走留下不知行情的同胞被騙。不是我冷酷,我真的管不了太多。雨絲毫沒有變小的趨勢,我把翻著戴的帽子正過來,往反方向走。遇到的小販大叔雖然比剛剛那位給的250rs每公斤要便宜50rs,我卻知道他還是多報了一倍的價。想著還要給杏仁和師父帶去,我挑好了六個芒果打算先斬後奏跟他砍價。沒想到大叔就是不鬆口。我和劉叔叔那次的六個芒果只花了400rs,大叔卻只說他的芒果更好。他為了說服我,還切了一小塊讓我嘗嘗他“質量很好”的芒果,我雖然拒絕還是被他塞了一塊。我不知道把皮扔到哪裡,大叔見狀一把拿過直接扔到了身後的地上。我的“please”和“I love you”砍價法在他這裡完全沒用,他只是大笑。倒是他身後的小哥受不了了,和我聊了聊每次聊天都會提到的名字家鄉年齡問題等有的沒的後順道幫我說話,想讓小販便宜。無奈小販也有他的幫手大叔,在旁邊一直誇芒果的又大又甜。我感覺我每次出門買東西,就好像是個黑幫個體戶,一個人和眾多幫派成員打太極。雨越下越大,卻不能泡軟小販叔那顆心,他一定覺得可以把我手裡的芒果高價賣給不懂行情的其他游客。即使我說我就住在對面那家旅館,你看我多誠意下雨還在這裡買,他也無動於衷。那我也不倒貼了,放下芒果說了句“不管怎樣謝謝了”,轉頭就走。我不想在鞋裡培養一片濕地,馬上回屋三下五除二拿了洗漱用品搶占公共浴室。想著我鎖了門,就把鑰匙也拿進了浴室,不想剛進浴室不久,杏仁就被擋在了門外。我像賊一樣又要大聲到讓她聽見鑰匙在我這裡,又要防著別人以為有個瘋子。但是杏仁辜負了我的個人演出,直接下了樓。後來她告訴我,那一聲聲敲門的不是她,嚇得我眼睛大了一倍。聽到有人上樓,我馬上穿戴好,推門一看真的是杏仁。我獃在衛生間不走,“晚上洗澡的人挺多的,趕緊回去拿東西,我給你占位置。”夜晚的單人床上,我們兩個單身女青年蜷縮著長談。為了利益虛情假意的朋友,善良得彆扭的 尼泊爾 人,賤得愚笨的女閨蜜,獃蠢的她的poonhill背夫……我們像兩個獨自轉著呼啦圈的人,生活沒有交集,也因為差著十歲很難有交集,可在一張床上的我們,卻可以有無盡的話題。和她的一夜,給我了很大觸動,這也是為什麼我把旅館攻略那一篇游記的標題 裡加 了一句,“我們只差一次孤獨”。杏仁說到高興時,會狠狠地打我一下,她道歉的樣子更像是誇自己,“我是體育生嘛。”我自然也拆穿她,“既然沒讀體校,那就是個子小沒考上咯。”其實文章里的名字,多半是真名里拼音開頭字母的重組,沒有太大意義。但是杏仁這個名字我覺得越叫越好聽,如果用一個詞形容這段旅程,我也會叫它杏仁。在 泉州 做外貿的杏仁得著甲肝,為了離過婚的男朋友打飛滴照顧他的孩子,也在深夜勇敢堅決的拒絕男人。男朋友不想讓她來 廣州 一起約會,她就“他奶奶的”罵著。我們越聊越起勁,即使她有潔癖,把手機墊在手紙上放在我身側充電我也沒嫌棄——要知道我的失眠就是因為睡覺時手機離腦袋太近——我們全盤托出了自己的感情經歷,當然我給的是空盤。她剛剛在找旅館時,男朋友拒絕了她去找他的意圖,兩人沒多說,也就散了。由此,我們談論了一系列男人話題。總在一個沉默的停頓,她會又想起什麼,“好吧,再告訴你點。”我是她感情的垃圾桶,從不拒絕她的傾倒。這晚,世界當著我們的面撕開了虛偽的麵皮,但是潰爛和假象並沒有流著粘稠的液體欲蓋彌彰。受傷了就是受傷了,不高興也就是不高興。這就是躺在一張床上的好處。我可以看到她不穿內衣的形體,她看的到我毫無掩飾的嘴臉,因為我倆睡的那張床不叫利益。除了在面對對象這件事上,從全球看,我倆是情敵,但更多的關係我們沒有。所以沒有刻意的惡意就是有了自然的善良。杏仁看我總是不顧形象的大笑和罵人,也放開了直說:“你知道嗎,第一次見你,看你面無表情一路沒說話的樣子,真的挺可怕的。”我雖然說我只是不高興那輛破車的狀態,心裡卻默默點頭。我承認我沒有表情的樣子像是立著的情感空殼,誰也別碰我,誰也別看我。高興我就自生自滅,不高興我就自暴自棄。在那個沒有破口的繭里,我高興我有我的世界,並不自怨自艾,也不沸騰膨脹。慢慢的,我們兩人漸漸安靜。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讓我們停止了對話,反正不是困倦。杏仁同意我在房裡留一盞燈,我倆背著身睡,因為怕臟,穿著外衣沒有蓋旅館的被子。我覺得今天是我最偉大的一天,我再一次證明我不輕易死。如果我沒記錯,本人就是當年那個化學一模57分把班級平均分在區 裡拉 低一個排名然後二模滿分的犟姑娘。今晚我真的很喜歡你,我要和你睡一覺。 我想記得你。那天我在書桌前,我前面有道陽光,我想看清黑板,陽光和我中間卻總隔著一個你。只要一抬頭,你的背影就是我小眼睛的全部。那時,書桌黑板窗帘都是新的,只有我們是舊的。我很想和你牽手出去在校門口照一張像,不用笑的那種。結果我們既沒有並肩,也沒有笑,甚至沒有同框——讓我把那層膜戳破,像捅開酸奶結成的那層膜一樣——我們並沒有出去照相,因為一切都太新了,你不在我眼前,我眼前也沒有陽光,甚至本人也沒有抬頭。但是我在,諷刺的是我在。我為什麼在什麼都沒有的地方臆想一場足以狗急跳牆的鬧劇?可能還是因為你,但是話說回來,你不在。所以就讓我在形形色色中虛虛實實恍恍惚惚,閃閃爍爍 中山 山水水生生死死,林林總總中心心念念渾渾噩噩,風風雨雨中紅紅火火紛紛揚揚。歲歲年年,日日月月,周而複始。
剛進屋的我正被極光嘲笑著來的正是時候,他要請將要離開的帳篷吃飯。我囑咐杏仁別忘鎖門後,把行李放下,沒多想就直接走了。這時我才意識到自己渾身是泥,鞋裡都可以養泥鰍了。在門外的公用衛生間,當著師傅極光的面,我腿在空中畫了個半圓直接落到池子里,我要在穿著褲子襪子和鞋的情況下把自己洗乾凈——剛剛咱可是過了泰米爾這條河——極光沒說話,他獃住了。帳篷見到我有點吃驚,她沒想再碰到我。雖然我是她好不容易碰到的女孩子,我倆卻互相不喜歡。她把朋友當導游以自我為中心。我第一次去博大哈佛塔就是和她一起的,她圍著極光瞎問,整個人控制著我們隊伍的速度和方向,在夢想花園時也是。不想留篇幅給她,我們氣場不合。吃飯的那家 重慶 餐館就在圓夢出門右拐不遠,菜價和國內一樣,但是味道挺不錯。店內好像沒開抽油煙機,四壁也沒有窗戶,我只能不停地咳嗽流眼淚。雖然看出了帳篷因為我打攪她這頓二人餐很不爽,我也沒走——能少花錢就少花錢,走到今天我經歷了太多,我不要臉,我要吃免費的晚餐。我們等菜的時候,服務員小哥一個ok揚手就走,正好讓我看見了他右腋下的衣服洞。真是副風景啊,小叢林剛好從裡面冒出來。我指給極光看,“這哥們兒腋下漏了個洞。”小哥雖然覺得我沒說好話,也不好意思多問,直接走掉了。但是極光反應比較大,把正喝著的一口水吐在了帳篷衣服上。到現在我還享受著有潔癖的帳篷的表情,好像我教唆豬把她的乾凈白菜給拱了一樣。就沖她這表情,這頓飯就是吃屎我也高興。飯菜馬上端上,但是帳篷半截就被一個路上遇到的姑娘叫去幫忙帶東西回國。我儘量剋制著貪吃的心,慢慢但不停地夾菜。回來時,一桌的菜剩的不多了,我提議和極光一起請帳篷,再點點兒菜,帳篷自然是婉拒了。我以為極光會送帳篷回去,結果倆人就在旅館前揮了個手,馬上分道揚鑣。送完她轉身進旅館的極光還在跟我說,“你個丫頭,來了也不告訴我一聲,我去接你啊。”我先告別了極光,想在路邊買芒果。 尼泊爾 的水果又大又甜,雖然裡面有時候會有點小蟲,吃的時候要註意一下,我也依舊難割捨對水果的愛。坦白講,我可以好幾個禮拜只吃水果過活,我也不是沒這麼乾過。連舍友都說我的胃會被這些小妖精搞壞,我也不管,我就是喜歡花錢買它們。它們長得那麼可愛,肥嫩多汁滿面紅光。我最高興的事就是在上午花兩個小時吃水果,看著它們水靈靈的倒在我的盤中,我最享受咬完一口後它們默默流下的汁水,有時因為擠破果肉而發亮的身體,它們沉默的樣子好像被我欺負的小姑娘。天啊,太爽了。但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我討厭香蕉和榴蓮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它們不好吃,是因為它們不可愛,被我欺負後沒有吐露真情,像個憨憨的傻兒子。總之,我愛水果,水果愛我!我在右拐直走,遇到了我在 尼泊爾 第一次買水果時的小販,他那張姦商臉我真的忘不了。我告訴他我們見過,他卻糊弄著說是的是的我記得,手裡擺弄著芒果眼睛瞟向別處。想到他上次想騙我錢的架勢和這次的虛高價,我轉頭就走留下不知行情的同胞被騙。不是我冷酷,我真的管不了太多。雨絲毫沒有變小的趨勢,我把翻著戴的帽子正過來,往反方向走。遇到的小販大叔雖然比剛剛那位給的250rs每公斤要便宜50rs,我卻知道他還是多報了一倍的價。想著還要給杏仁和師父帶去,我挑好了六個芒果打算先斬後奏跟他砍價。沒想到大叔就是不鬆口。我和劉叔叔那次的六個芒果只花了400rs,大叔卻只說他的芒果更好。他為了說服我,還切了一小塊讓我嘗嘗他“質量很好”的芒果,我雖然拒絕還是被他塞了一塊。我不知道把皮扔到哪裡,大叔見狀一把拿過直接扔到了身後的地上。我的“please”和“I love you”砍價法在他這裡完全沒用,他只是大笑。倒是他身後的小哥受不了了,和我聊了聊每次聊天都會提到的名字家鄉年齡問題等有的沒的後順道幫我說話,想讓小販便宜。無奈小販也有他的幫手大叔,在旁邊一直誇芒果的又大又甜。我感覺我每次出門買東西,就好像是個黑幫個體戶,一個人和眾多幫派成員打太極。雨越下越大,卻不能泡軟小販叔那顆心,他一定覺得可以把我手裡的芒果高價賣給不懂行情的其他游客。即使我說我就住在對面那家旅館,你看我多誠意下雨還在這裡買,他也無動於衷。那我也不倒貼了,放下芒果說了句“不管怎樣謝謝了”,轉頭就走。我不想在鞋裡培養一片濕地,馬上回屋三下五除二拿了洗漱用品搶占公共浴室。想著我鎖了門,就把鑰匙也拿進了浴室,不想剛進浴室不久,杏仁就被擋在了門外。我像賊一樣又要大聲到讓她聽見鑰匙在我這裡,又要防著別人以為有個瘋子。但是杏仁辜負了我的個人演出,直接下了樓。後來她告訴我,那一聲聲敲門的不是她,嚇得我眼睛大了一倍。聽到有人上樓,我馬上穿戴好,推門一看真的是杏仁。我獃在衛生間不走,“晚上洗澡的人挺多的,趕緊回去拿東西,我給你占位置。”夜晚的單人床上,我們兩個單身女青年蜷縮著長談。為了利益虛情假意的朋友,善良得彆扭的 尼泊爾 人,賤得愚笨的女閨蜜,獃蠢的她的poonhill背夫……我們像兩個獨自轉著呼啦圈的人,生活沒有交集,也因為差著十歲很難有交集,可在一張床上的我們,卻可以有無盡的話題。和她的一夜,給我了很大觸動,這也是為什麼我把旅館攻略那一篇游記的標題 裡加 了一句,“我們只差一次孤獨”。杏仁說到高興時,會狠狠地打我一下,她道歉的樣子更像是誇自己,“我是體育生嘛。”我自然也拆穿她,“既然沒讀體校,那就是個子小沒考上咯。”其實文章里的名字,多半是真名里拼音開頭字母的重組,沒有太大意義。但是杏仁這個名字我覺得越叫越好聽,如果用一個詞形容這段旅程,我也會叫它杏仁。在 泉州 做外貿的杏仁得著甲肝,為了離過婚的男朋友打飛滴照顧他的孩子,也在深夜勇敢堅決的拒絕男人。男朋友不想讓她來 廣州 一起約會,她就“他奶奶的”罵著。我們越聊越起勁,即使她有潔癖,把手機墊在手紙上放在我身側充電我也沒嫌棄——要知道我的失眠就是因為睡覺時手機離腦袋太近——我們全盤托出了自己的感情經歷,當然我給的是空盤。她剛剛在找旅館時,男朋友拒絕了她去找他的意圖,兩人沒多說,也就散了。由此,我們談論了一系列男人話題。總在一個沉默的停頓,她會又想起什麼,“好吧,再告訴你點。”我是她感情的垃圾桶,從不拒絕她的傾倒。這晚,世界當著我們的面撕開了虛偽的麵皮,但是潰爛和假象並沒有流著粘稠的液體欲蓋彌彰。受傷了就是受傷了,不高興也就是不高興。這就是躺在一張床上的好處。我可以看到她不穿內衣的形體,她看的到我毫無掩飾的嘴臉,因為我倆睡的那張床不叫利益。除了在面對對象這件事上,從全球看,我倆是情敵,但更多的關係我們沒有。所以沒有刻意的惡意就是有了自然的善良。杏仁看我總是不顧形象的大笑和罵人,也放開了直說:“你知道嗎,第一次見你,看你面無表情一路沒說話的樣子,真的挺可怕的。”我雖然說我只是不高興那輛破車的狀態,心裡卻默默點頭。我承認我沒有表情的樣子像是立著的情感空殼,誰也別碰我,誰也別看我。高興我就自生自滅,不高興我就自暴自棄。在那個沒有破口的繭里,我高興我有我的世界,並不自怨自艾,也不沸騰膨脹。慢慢的,我們兩人漸漸安靜。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讓我們停止了對話,反正不是困倦。杏仁同意我在房裡留一盞燈,我倆背著身睡,因為怕臟,穿著外衣沒有蓋旅館的被子。我覺得今天是我最偉大的一天,我再一次證明我不輕易死。如果我沒記錯,本人就是當年那個化學一模57分把班級平均分在區 裡拉 低一個排名然後二模滿分的犟姑娘。今晚我真的很喜歡你,我要和你睡一覺。 我想記得你。那天我在書桌前,我前面有道陽光,我想看清黑板,陽光和我中間卻總隔著一個你。只要一抬頭,你的背影就是我小眼睛的全部。那時,書桌黑板窗帘都是新的,只有我們是舊的。我很想和你牽手出去在校門口照一張像,不用笑的那種。結果我們既沒有並肩,也沒有笑,甚至沒有同框——讓我把那層膜戳破,像捅開酸奶結成的那層膜一樣——我們並沒有出去照相,因為一切都太新了,你不在我眼前,我眼前也沒有陽光,甚至本人也沒有抬頭。但是我在,諷刺的是我在。我為什麼在什麼都沒有的地方臆想一場足以狗急跳牆的鬧劇?可能還是因為你,但是話說回來,你不在。所以就讓我在形形色色中虛虛實實恍恍惚惚,閃閃爍爍 中山 山水水生生死死,林林總總中心心念念渾渾噩噩,風風雨雨中紅紅火火紛紛揚揚。歲歲年年,日日月月,周而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