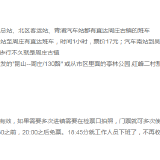小板凳出品|| 私語吳哥


眯起眼,只見兩株 大樹 扎根於廢墟上,以詭異的姿態高聳入雲。 巴戎寺:微笑大清早來到一座山門口,迎接我們的不是迷人澄凈的微笑,而是兩座威武的大 石獅 子。
這是巴戎寺,需要爬山的?隱隱覺得不對勁,但還是想一探究竟。
可這道貌似沒有盡頭,越爬心中的疑問越大,越發不安。汗水順著灼熱的皮膚滾下,再落到滿是土的山道上。沒有留司機的電話,騎虎難下。眼看越來越熱,終於認輸,灰溜溜下山。
原來我們把巴戎寺標註成了巴肯山,盡顯學渣本色。


避讓、等待,烈日炎炎,心浮氣躁。
陽光漸漸強烈,笑容慢慢消失。
沒有好好看一眼精美的浮雕,甚至沒有與微笑的佛面更近距離的接觸,只有滿心的失望和懊悔。


既不懂隨遇而安,也不會心甘情願,終究是少年性子。 巴芳寺:佛不語


巴芳寺遠不如吳哥寺、巴戎寺那樣名聲在外,我們也沒有太多的期待,就這樣漫不經心地來了。
遠遠便望見寺廟頂部立著一座座類似門框一樣的建築 ,並不明白建築者的真正意圖。只覺得這門亦然與天空連接,索性,取名為“天空之門”。仿佛穿過這扇門,就能穿越時空,門後有另一個世界,另一個自己。
陽光和煦的 春日 ,暖哄哄的感覺讓人昏昏欲睡。踏著腳踏車悠然歸家,媽媽和爸爸正在廚房忙碌,鍋碗瓢盆勺撞擊發出悅耳的叮叮噹當,油鍋里的滋滋聲,奏響著家庭最美的樂章。還有奶奶,微笑著召喚,小心翼翼掏出一團乾凈繡著花兒的手帕,展開,幾顆紅艷艷的櫻桃……



三個小家伙不知何時來到我們旁邊,好奇地打量我們。




走過長長的引道,每一步都充滿儀式感。等真正登上第二層不一會兒,工作人員開始催趕我們離開,出口在寺廟背後。
猝不及防地,眼睛的景象讓沒有好好做功課的我們,恍了神。

來或者不來,你都在這裡。
這是一尊用石塊堆砌而成的卧佛。
佛身殘缺不全,神情模糊,但我知道他正註視著我們,默默地。
天空之門依然矗立在上,只是不知究竟是佛馱起了這門,還是門壓制了佛。

問曰:既然愛別離,怨憎會,撒手西歸,全無是類。不過是滿眼空花,一片虛幻。又何來愛?何必愛?又何來恨?何必恨?又何來愛生恨?何必愛生恨?
問曰:既然種如是因,收如是果,一切唯心造。為何世間又有太多事有違此理?好人不得善終?惡人卻活得如此瀟灑?
問曰:既然美麗容顏只是虛幻,世間人又何必分美醜?
問曰:佛若有情,何來六根清凈?佛若無情,又豈會生普度眾生之心?
問曰:既然緣起即滅,緣生已空,那麼緣又有何意義,難道只為思之苦?
問曰:佛一直勸人放下執著,這是不是也是一種執著?
問曰:佛既普渡眾生,為何又只渡有緣之人?
佛曰:不可說。
在催促聲中,匆匆別離。
不舍,緣止。


恍惚中,突然聽見小伙伴低聲呼喚,帶著驚喜。定睛一看,在黑黢黢的石塊堆里,一簇小苗強勢探出,格外油綠新鮮。
慶幸,懶得做功課,卻有了更多的驚喜和領悟;
遺憾 ,沒能爬上去,上面又是何等的風光?
或許,我本只能深深地仰望你。
塔布隆寺:重生


是的,我知道美好的總會失去,
但我卻答應過我會等他回來,
因為我傻,我不肯放棄。
所以我成了一個妖精。
漫長的等待中,
風吹散了我的頭髮,吹朽了我的皮膚,吹化了我的身體,
只剩下一個等待的姿勢,
白森森地立著,
用沒有眼球的黑洞望向天涯。
——《悟空傳》





這不是那棵開花的樹,慎重、美好,情意綿綿,
也不是 托斯卡納 的那棵樹,沒有思想,沒有心,只有對 托斯卡納 深沉的熱愛。
這是怎樣的樹?
野蠻、孤傲,力量磅礴,能屈能伸。


無論以怎樣扭曲的姿勢,
無論石塊有多麼的堅不可摧,
無論恢宏精美的宮殿依仗了誰的庇護,
塔布隆的樹蔑視一切,傲慢地伸出巨大的爪子,一點點侵入,一寸寸吞噬,向下延伸,向上挺立,日復一日。
這場較量歷日曠久,兩股力量死死糾纏,相互抵抗,直至血乳交融。
看不清到底是樹在夾縫中苦苦求生,還是樹里生生蹦出了一座神廟。


腐朽的磚牆和蓬勃的新生命,
殘垣斷壁的死寂和野蠻生長的力量,
構成了眼前動人心魄的世界,
一半陰暗,一半明媚,
一半頹廢,一半盎然,
既矛盾又和諧,直抵入心,不可方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