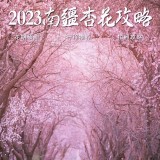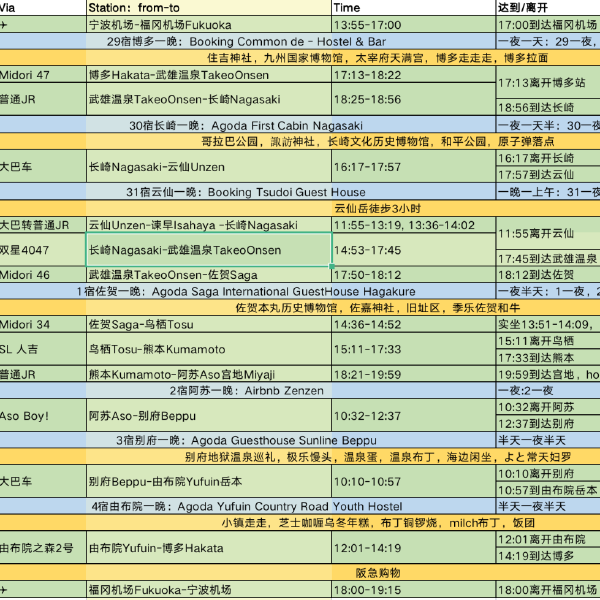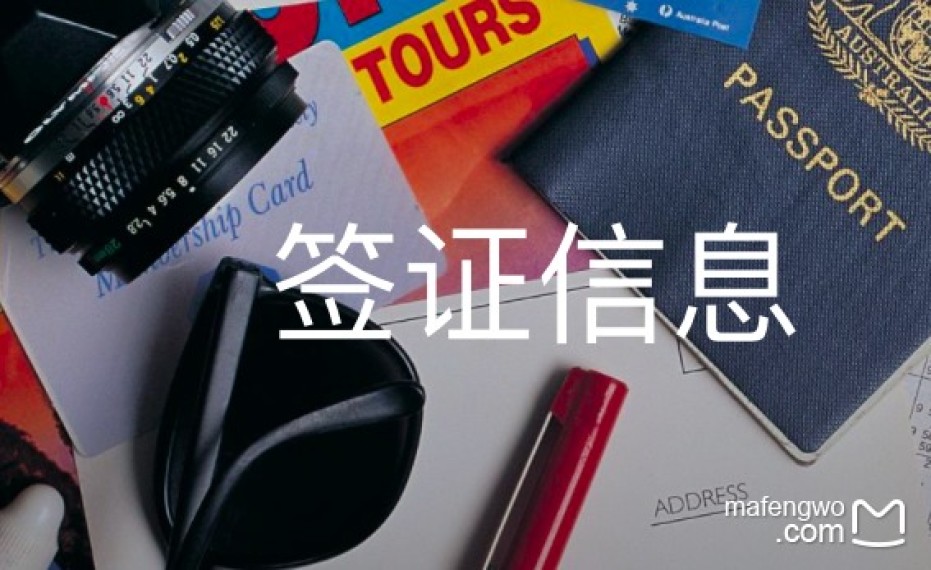*毛小主鏡頭下的世界*第八章—澳大利亞[Australia] 蜜月偽裝下一場漫無目的的隨意行走




所以,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起點。還是那個南十字星,還是那個機場。告別的心境卻大不相同。
等待登機時,我思考著要不要聯繫在 悉尼 的朋友,翻開朋友圈,想想也是自從大學畢業就沒聯繫過,還是又鎖上了屏幕。
然後,起飛,飛行,落地。
不知道為什麼,在看到 悉尼 歌劇院和海港大橋的那一刻,突然間對這個城市沒了期待。或許很多人心中的 悉尼 就是這兩個地方,看到了,還有什麼能去發現,忽然不知道了。
即使搭上地鐵真的被 悉尼 所包圍時,也沒有激發我的興緻。我記得,那份丟失的游記草稿,也是寫到差不多的位置,可能連寫下去的興緻也不高。 快進悉尼 ,時刻有一種快進的錯覺,時間過得快,行走速度也快。這速度一定是被路上跑著的人傳染了。
這之後的故事其實都很模糊了,因為前面的故事寫過兩遍也順便回憶兩遍,也因為後面親戚的拜訪,好像那幾天唯一的感受就是不舒服別惹我。
你看,我連寫都不消多用幾句話。
不過我是沒想到,這份匆匆里,也帶著些驚喜。
接下來,走出熱鬧的酒店,走向熱鬧的街道。 Circular Quay一個真的遇到郵輪停泊的碼頭。還不是一次,是很多次。
看見一次,就和趙先生聲明一次一定要坐郵輪的主張。

這就是為什麼永遠那麼熱鬧,若是擺上些小攤,怕是快能進化成廟會了。
如果執念於兩個地標性建築,那這裡真的可以滿足,一側一種風景。


於是,我們只是在下麵以一種仰視的角度仔細看了看,甚至都沒有走上橋,好像幾天來也沒有機會讓我找到橋的入口。
在下麵反而收穫挺有意思的視角,看著那些攀橋人的小心翼翼,看著健身狂人的戰繩訓練,看著情侶躲藏的卿卿我我。


我查過維基百科,故意去看了英語版,講得很詳細。
那天我選擇了一場電影交響樂演出,這個名字是我起的,因為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形容這種演出形式。
伴隨著電影莫扎特傳,所有音樂均由交響樂團現場演奏。
電影已經相當不錯,看完讓我想更多去瞭解莫扎特。交響樂團的演奏更是驚為天人,以致於結束後,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還帶有贊揚的口哨聲和吶喊聲,不誇張。
以前總在書上讀到,某某贏得了雷鳴般的掌聲,這大概就是那種感覺。

體感上似乎比 墨爾本 皇家植物園大出許多,很多人在跑步,很多。園裡實際上沒有什麼花,更多的是樹。

我是用了兩次,才算湊合走完。

我試圖尋找格外激動的當事人,沒有找到。

因為走錯了方向,選擇繞遠路線。
我為什麼在這裡說這個,因為這些陰差陽錯,讓我在茫茫人海中遇見大學時期的朋友。沒錯,就是那個前一天還猶豫要不要聯繫的朋友。
你說,世界是不是很小,緣分是不是很妙。
就是這場奇妙的偶遇,讓我餘下的一天都十分亢奮,頂著親戚來訪隱隱疼痛的肚子,暴走了一天。
當我們終於找到方向,開始走上正軌時,我又被一個游客中心吸引。事實證明,在 澳大利亞 的十四天里,我見到最別緻的明信片,就是在這裡。
這是好心酸的一句話啊,整個 澳大利亞 ,竟然只有這裡有符合我審美的明信片。
好吧,不重要,在被無數事情分散精力後,我終於到達目的地。類似是環形碼頭的複製粘貼,只是更清靜一點。
好像一句話已經概括了它的全部精髓。


去之前,我其實更多的是畏懼,我害怕和厭惡地上黑乎乎的髒水,也不喜歡濃郁的海鮮腥氣。


調查過口碑,但還是猶豫良久才最終選定。
雪蟹,蝦,龍蝦,海膽,該吃的都吃到,而且是原生態的口味。加工費這種東西,我們不需要。



環境還算不錯,有很多孩子在廣場上玩滑板,儘管寫著不許。




去翻了官方網站的日曆才想起那是個叫Mikala Dwyer的藝術家,她的作品重新定義了那些我們熟悉的材料,以及它們所表達的世界。感覺是一個可以玩的展覽。



寫到這感覺自己被遺憾感淹沒了,還有點兒想哭。

不過說實話, 悉尼 ,並沒有很適合購物。
所以,就當作是個景點在看。

那天有微微的風,已經預感不會是平靜的一次觀鯨體驗,誰想到是那麼不平靜。
上船時自信滿滿的選擇了室外二層平臺,還假裝有經驗的樣子說要隨著浪搖擺,這樣就不會暈船。
前面兩小時都非常清醒,還追著鯨魚出現的方向滿船跑。
然而,事情的轉折就出現在一隻躍出水面且轉體一周的鯨魚沒有拍到,此後我們就開始在公開海域的尋覓與飄蕩。與其說飄蕩,或許水上飛更貼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