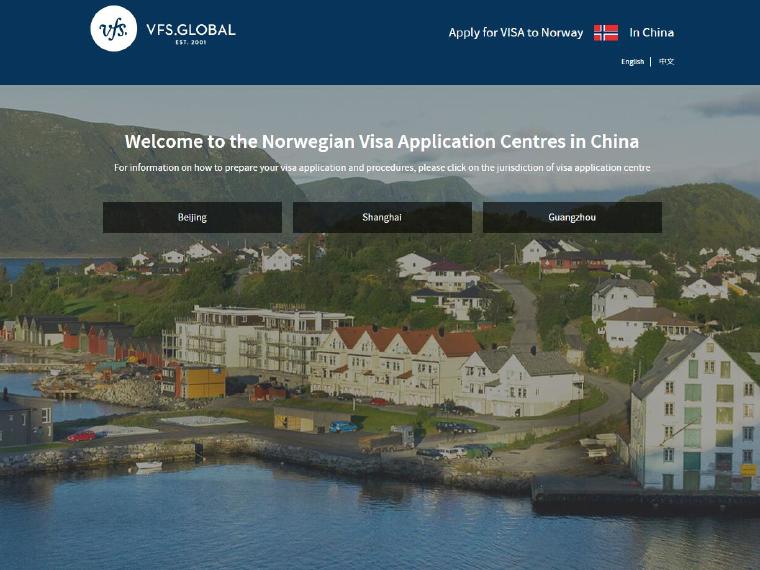Geneva:旅途中的貴人
迷路,是我和 日內瓦 的第一類接觸。根據旅館地圖的指引,它離車站不過五分鐘腳程,我卻拖著三十公斤的大行李,走了三十分鐘才聽到一句法式濃腔的歡迎光臨。
那是一幢四層樓的小旅店,黑人經理仿佛用鼻子說話似的,熱切地向我說明相關設施和規定。它其實沒什麼設施,一層樓三間房,共用一間衛浴,房間內有一張書桌、一張床、和一個洗手台,剩下就是一條走道。說來你或許不信,這般寒愴的房間一晚居然要價三千塊新臺幣! 置妥行李後,我感覺到腹部一陣空虛。時已午後三點,肚子里的早餐麥片早已消化殆盡,我上街塞了個巧克力香蕉可麗餅果腹,之後隨意走過凋零的花鐘和衝天的噴泉。或許是漫天陰雲作祟,或許是心懸明天和客戶的會面,我走得意興闌珊,走得淡而無味。天色將暗時,我簡單地買了生菜 沙拉 和麵包,以及一小瓶01年的馬哥村葡萄酒—紅石榴色的艷麗 光澤 、黑醋慄和各種莓果混合的豐富香氣、優美醇厚的口感—這些感官早已成為我行走 歐洲 時最大的期待和安慰。
置妥行李後,我感覺到腹部一陣空虛。時已午後三點,肚子里的早餐麥片早已消化殆盡,我上街塞了個巧克力香蕉可麗餅果腹,之後隨意走過凋零的花鐘和衝天的噴泉。或許是漫天陰雲作祟,或許是心懸明天和客戶的會面,我走得意興闌珊,走得淡而無味。天色將暗時,我簡單地買了生菜 沙拉 和麵包,以及一小瓶01年的馬哥村葡萄酒—紅石榴色的艷麗 光澤 、黑醋慄和各種莓果混合的豐富香氣、優美醇厚的口感—這些感官早已成為我行走 歐洲 時最大的期待和安慰。  隔天天色未明,我又拉著沉甸甸的行李箱出門。原本安排了計程車到東南市郊的Eaux-Vives車站,但由於前晚丹寧慫恿,我錯過了兌幣站的打烊時間,算一算手上只剩幾枚法郎銅板,且聽說計程車不收歐元,我只好晃點司機,提早摸黑上路。到了轉角的公車站,我實在沒耐性理清看板上的班車資訊,眼見四下無人,正索性徒步前往,此時來了一個老先生,我抓緊機會開口:
隔天天色未明,我又拉著沉甸甸的行李箱出門。原本安排了計程車到東南市郊的Eaux-Vives車站,但由於前晚丹寧慫恿,我錯過了兌幣站的打烊時間,算一算手上只剩幾枚法郎銅板,且聽說計程車不收歐元,我只好晃點司機,提早摸黑上路。到了轉角的公車站,我實在沒耐性理清看板上的班車資訊,眼見四下無人,正索性徒步前往,此時來了一個老先生,我抓緊機會開口:
Parle vous angleis? (您說英語嗎?)
開口前我早已心知肚明。果然,老先生搖搖頭。我不死心,繼續用彆腳的法語單字和他溝通,試圖問出開往目的地的公車線路。後來老先生示意我跟他上車,下車,再指引我轉乘電車的位置和車號,並告訴我電車的終點站就是我要尋找的目的地。呵,原本我還天真地想徒步前進,若沒有這位好心老伯的指點,我可能踏破鐵鞋還在手足無措地尋覓路標。他是我在 日內瓦 遇到的第一位貴人。
電車抵達Eaux-Vives車站時,天色還是黑壓壓的一片,隱約可辨它的狹促、簡陋、陳舊。我推開褪漆的木門,嘎嘎的聲響驚動了室內一團黑影,一位邋遢的游民弓起身來乜了我一眼,旋即又蜷回夢鄉。我在昏黃的光線下釐清班車時刻和購票機的操作說明,然後小心翼翼地遁入角落,安靜地等待火車靠站。直到列車將駛前十分鐘,隨著另一陣嘎嘎聲,整個空間才闖入第三個人影。
Parle vous français? (您說法語嗎?)
一身輕裝的年輕人指著投幣式購票機,茫然不解地朝我發問。我搖搖頭,同時心中納悶,這是什麼鳥站,連當地人也對它如此生疏。我用英文向他解釋如何操作機器,並詢問是否能和他兌換法郎。他說他身上沒有零錢,暗示我跟他一起走。我們到對街的咖啡店兌換零錢,他慷慨地請我一杯咖啡和一塊可頌表達謝意。我們回到了車站,買了票,繼續等待。 離火車開車時刻已過了十幾分鐘,整個月臺兀自如被遺棄了般,毫無風吹草動。年輕人打了電話,驚覺鐵路罷工,沒有人知道下一班火車什麼時候啟動。這種法式散漫,真叫人不敢恭維。我提議搭計程車,可以一起分擔車資。他說再等到下一班車的公告時間看看。隨後他看到車站外停了一輛旅游巴士,於是踱過去和司機交談。後來,他告訴我這輛巴士開往Annecy,正是我今天訪客的地點。可惜並沒有開往他的目的地。我上了車,向我的第二位貴人道了再見。
離火車開車時刻已過了十幾分鐘,整個月臺兀自如被遺棄了般,毫無風吹草動。年輕人打了電話,驚覺鐵路罷工,沒有人知道下一班火車什麼時候啟動。這種法式散漫,真叫人不敢恭維。我提議搭計程車,可以一起分擔車資。他說再等到下一班車的公告時間看看。隨後他看到車站外停了一輛旅游巴士,於是踱過去和司機交談。後來,他告訴我這輛巴士開往Annecy,正是我今天訪客的地點。可惜並沒有開往他的目的地。我上了車,向我的第二位貴人道了再見。
五十人座的巴士只坐了我一個乘客,這是我的旅行專車。司機請我吃了個糖,告訴我由於鐵路罷工,所以他被派來支援轉乘的旅客,因此車資免費。我們信口談天,他說 法國 人通常高傲冷漠,像他如此友善的算稀有動物。我想起 巴黎 人的嘴臉,心有戚戚焉。望向窗外,十一月的乍寒時節,下起了入冬第一場雪。巴士一路開進山裡,並朝更高更小的山徑前進。我心懷忐忑,Annecy應該不算小地方,怎麼司機逕自往荒郊野外駛去?該不會遇上了怪胎,錶面上如綿羊般和善,骨子裡卻藏著豺狼的噁心?我撥了通越洋電話給助理,笑說如果半天沒有我的音訊,就趕緊替我報警。
司機問我此行的目的。我告訴他客戶的公司名稱。霎時間,幸運女神又眷顧了我,司機說我們將經過那家公司,因此無須先到Annecy再搭計程車折返。我心底暗自歡呼,不只搭上免費專車,而且還是直達車;原本緊張的神經也頓時放鬆,司機還是純潔如羊,是我自個兒居心不良。隨著爬坡的高度越陡,窗外的雪越下越大,當我在山頂上下車時,大地早已冰如雨下,白雪橫飛。我向第三位貴人鄭重道謝,轉身走進漫天冰雪中,一歩一哆嗦地走向客戶公司。
原以為客戶的公司應該位於市區里的辦公大樓,沒想到居然整片山頂都是客戶的運籌總部。和客戶初次見面,我訴說起一早的冒險和奇遇,客戶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回應我:不是早叫你搭計程車嗎?

那是一幢四層樓的小旅店,黑人經理仿佛用鼻子說話似的,熱切地向我說明相關設施和規定。它其實沒什麼設施,一層樓三間房,共用一間衛浴,房間內有一張書桌、一張床、和一個洗手台,剩下就是一條走道。說來你或許不信,這般寒愴的房間一晚居然要價三千塊新臺幣!
Parle vous angleis? (您說英語嗎?)
開口前我早已心知肚明。果然,老先生搖搖頭。我不死心,繼續用彆腳的法語單字和他溝通,試圖問出開往目的地的公車線路。後來老先生示意我跟他上車,下車,再指引我轉乘電車的位置和車號,並告訴我電車的終點站就是我要尋找的目的地。呵,原本我還天真地想徒步前進,若沒有這位好心老伯的指點,我可能踏破鐵鞋還在手足無措地尋覓路標。他是我在 日內瓦 遇到的第一位貴人。
電車抵達Eaux-Vives車站時,天色還是黑壓壓的一片,隱約可辨它的狹促、簡陋、陳舊。我推開褪漆的木門,嘎嘎的聲響驚動了室內一團黑影,一位邋遢的游民弓起身來乜了我一眼,旋即又蜷回夢鄉。我在昏黃的光線下釐清班車時刻和購票機的操作說明,然後小心翼翼地遁入角落,安靜地等待火車靠站。直到列車將駛前十分鐘,隨著另一陣嘎嘎聲,整個空間才闖入第三個人影。
Parle vous français? (您說法語嗎?)
一身輕裝的年輕人指著投幣式購票機,茫然不解地朝我發問。我搖搖頭,同時心中納悶,這是什麼鳥站,連當地人也對它如此生疏。我用英文向他解釋如何操作機器,並詢問是否能和他兌換法郎。他說他身上沒有零錢,暗示我跟他一起走。我們到對街的咖啡店兌換零錢,他慷慨地請我一杯咖啡和一塊可頌表達謝意。我們回到了車站,買了票,繼續等待。
五十人座的巴士只坐了我一個乘客,這是我的旅行專車。司機請我吃了個糖,告訴我由於鐵路罷工,所以他被派來支援轉乘的旅客,因此車資免費。我們信口談天,他說 法國 人通常高傲冷漠,像他如此友善的算稀有動物。我想起 巴黎 人的嘴臉,心有戚戚焉。望向窗外,十一月的乍寒時節,下起了入冬第一場雪。巴士一路開進山裡,並朝更高更小的山徑前進。我心懷忐忑,Annecy應該不算小地方,怎麼司機逕自往荒郊野外駛去?該不會遇上了怪胎,錶面上如綿羊般和善,骨子裡卻藏著豺狼的噁心?我撥了通越洋電話給助理,笑說如果半天沒有我的音訊,就趕緊替我報警。
司機問我此行的目的。我告訴他客戶的公司名稱。霎時間,幸運女神又眷顧了我,司機說我們將經過那家公司,因此無須先到Annecy再搭計程車折返。我心底暗自歡呼,不只搭上免費專車,而且還是直達車;原本緊張的神經也頓時放鬆,司機還是純潔如羊,是我自個兒居心不良。隨著爬坡的高度越陡,窗外的雪越下越大,當我在山頂上下車時,大地早已冰如雨下,白雪橫飛。我向第三位貴人鄭重道謝,轉身走進漫天冰雪中,一歩一哆嗦地走向客戶公司。
原以為客戶的公司應該位於市區里的辦公大樓,沒想到居然整片山頂都是客戶的運籌總部。和客戶初次見面,我訴說起一早的冒險和奇遇,客戶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回應我:不是早叫你搭計程車嗎?